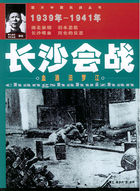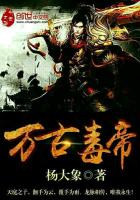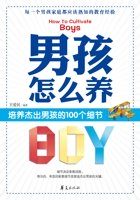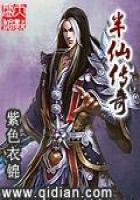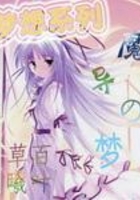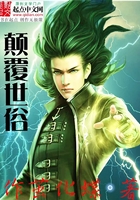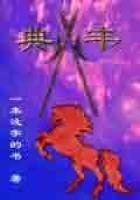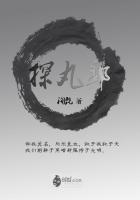刘畅不知道随着他的到来,刘备破釜沉舟的想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打算提前传位于他。要是知道,他就不会有如履薄冰的感觉,也不用每日为蜀汉前途焦虑不安了。
有刘备承上启下,他可以顺利地掌握朝政,荆州旧人、蜀中官吏也会归心于他。
正因为刘畅不知道,所以他急着上路,与关兴等人相处的时间长着呢,几个青毛头还怕摆不平,这时代君臣关系是非常严肃的,他主动折节下交,这几个小将怎会不感激涕零。
刘畅和众人寒暄几句,便在刘备的千叮咛万嘱咐下启程上路。
刘畅原打算逛逛CD的街市,从街市上卖的东西,可以看出百姓的生活质量,但由于先前耽搁了过多的时间,他怕赶不及铁匠们呈上他交待下去让他们做的仪器,误了大事,所以直奔城门,路上走马观花地看了看。
CD城的正门是南门,这是天底下中国式城池的固定修建方式。
春秋时期,全国各地开始兴起组成的高潮,而此前建有城墙的城市并不是很多,这也是受周礼的影响。
当时城墙多夯土为墙,大城城墙厚达十步,齐国临淄、燕国下都等都城城墙厚达二十步,间以瓷瓦排水道。城门道更是深达五十步至八十步,厚重幽长。
周礼规定:天子十二里,大国九里,次国七里,小国五里之城,体现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又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可是春秋战国时候,各国征战不休,哪会真正去遵守这些规定,各国城墙纷纷逾制,城墙厚度、高度、长度不断创造新高。
CD正是这样自行建造的作品,在秦代,城墙周长就达十二里,刘焉用张鲁阻塞蜀道为由,不再向朝廷进贡,首开军阀割据先例。CD在他父子两代人的苦心经营下,城墙一再加高加固,外墙已开始采用砖石砌就,城门道长达八十余步,道壁火把照明,城门选用厚重结实的楠木,外衬牛皮、铁皮,要八个人才能推得动。
刘畅一边四下观望百姓民居,一边津津有味地听董允地介绍,赵云、关兴等人相随于后,他们或是常年征战,或是潜心习武,对经史掌故了解甚少,一时也是听得兴趣盎然。
街上行人很多,既有麻衣葛服的百姓,也有锦袍绫罗的富户,还有不少高鼻深目皮肤黝黑手牵驮马骆驼的商贾。
刘畅极为惊讶,指着那些人问董允:“他们是什么人?似乎不是我朝人物。”
董允一见:“殿下所言甚是,这些不是我中土人士,他们是从大食来的商人,我大汉的蜀锦甚受他们国内达官贵族喜欢,价格奇高。从我国内购买,回去可得十倍之利,故虽路途遥远,商贾也是往来不绝。”
“可有我国内人向彼国贩卖?”刘畅看看这些最早的丝绸之路的使者,又转头瞧向街铺。这时候的街铺不像现代,有玻璃门窗柜台,店铺都是木板门铺,白天卸下一块块的木板堆放在旁边,出售的商品都堆放在店内一块大门板上供客人选购。
“这倒未曾听闻。”
“为什么?”刘畅愣了一下,回过头问到。
十倍之利啊,蜀国的人都富裕到这个地步了吗,十倍之利也不动心!要在他来的那个时代,十倍之利可以让人心动杀心了。
“殿下有所不知,蜀人恋土,不愿远行。刘璋父子治蜀宽厚,百姓大都足够生活,当然不愿到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这一路上有很多的危险,有狼虫虎豹、险滩、蛮族、盗贼,有多山高林密之地,瘴气厉害,杀人无形,如不是走投无路,蜀人是不会去从事这门风险极高的行业的。”
“可惜可惜。”刘畅连声感叹。他想自己是否有必要组织一支官方的商队,这么好赚的钱,不赚白不赚。
“殿下可是有意组织一支官方的商队?”董允看刘畅沉吟不语,猜出了他的想法。
“是啊,我大汉百废待兴,要用钱的地方多得很,有条赚钱的财路,却给他人实在可惜了。休昭可有计议?”
身后许久没有说话的黄皓接道:“殿下居心宅厚,体恤百姓,实在是我大汉之福。”
刘畅纵声长笑:“黄皓,你这个马屁就拍错了,我只是见不得钱被别人赚去了心痛而已!”
随行众人都是一阵哄笑,原本有些拘束的赵统、赵广也开始放松下来。
董允鄙视地瞪了黄皓一眼,说道:“这个可难。CD沃野千里,良田万顷,养活蜀中官民绰绰有余。殿下,我益州二百万丁口,只CD就有三十万人,CD以及周边广汉、绵竹、德阳,全国泰半人丁居住于此,其余分居梓桐、江州各郡,益州、云南郡地阔人稀,所住的人多仅上万,少则数千,为什么,就是无法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在那里生活的,多数还是代代居住于此的当地土人。殿下想要组建商队,除了这些土人,汉民难以达到殿下要求。而大宗货物,又怎么能放心交给这些土人去办呢,所以还请殿下三思!”
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刘禅面前说过这么多的话,而刘禅也从来没有耐心地听完过他的见解,现在得到刘畅虚心求教,大感兴奋,滔滔不绝。
董允看看刘畅还在深思,整顿思路,又委婉说道:“殿下意欲组织商队,无非是为国库充裕。其实蜀锦之物,中原、江东官吏富户都很喜欢,蜀锦之名,达于天下。殿下只需向两地贩卖,即可获利甚丰。”
刘畅微笑颔首,又摇摇头:“休昭见识多,道理也说得很透彻。我不是仅仅考虑到这一点而已。”
谈说之间,众人纵马出得城门。
由于没有护城河,城门外一条笔直的官道两旁,靠近城墙处有些集市店贩酒肆之外,大片大片的都是翻垦的农田,一栋栋农居散居各处,向外辐射。
刚刚秋收过后,田地里垛满了一堆堆的稻谷,在亮晃晃的阳光下金光灿灿。
刘畅一收马缰,开颜笑道:“又是一个丰收年啊,百姓们也该了开怀了吧。”
董允淡淡笑笑:“大概吧。”语气平淡。
刘畅疑惑道:“大汉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休昭似乎不是很高兴。”
董允欲言又止:“董允不敢。”
“讲!”刘畅敛颜肃然道,他身材浑厚,太子身份,自然流露一股威严。
“是!”董允一惊,急忙把心中所想和盘托出,“益州靠了秦李冰父子所修都江堰之福,将以前的洪涝之地开垦为千里沃野。自秦以来,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比较中原之地可称富足,谓之以天府之国。兼之山川闭塞,秦灭、绿眉暴乱、董卓乱朝以至诸侯战乱,皆未波及蜀地,虽与张鲁征伐经年,祸患仍不甚严重,百姓生息繁衍。然而与之相对,历代蜀地官员,待民都过于宽厚,门阀豪族兼并土地之风也从未得到有效治理,田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
董允一指远方,众人随他所指方向,看见一座庞大的庄园:“那是关内侯法邈的庄园,殿下适才所见,尽是他的田地。百姓辛劳,而所获皆归于豪族,百姓乐否?”
赵云眉头一雏,关兴、关索、赵统、赵广大吃一惊,关索咂舌道:“乖乖,这么多的地都是他们家的,他是谁啊,这得有多少地啊?”
“他有多少地,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不只是CD附近,就是绵竹、汉中,都有他许多田地。”董允无所谓地接着说:“至于他么,乃是故尚书令、护军将军,翼侯法正之子。”
“百姓们呢?他们自己没有地么,干吗不种自己的地而跑来当豪族的佃农?”问话的是赵云,他在诸葛亮那里知道一些蜀汉的现状,不过那是一个个数字,只有当亲眼所见,才能感受到赤裸裸的震撼!
“是啊,CD既然是沃野千里,士族豪绅能占的土地总是有限的吧,老百姓总还是有土地可耕种的。”赵广眼睛瞅着刘畅,怯生生地插话。
董允闭上双眼,沉重地问:“赵小将军,你知道什么是门阀么?”不待赵广回答,又用低沉地声音自问自答道:“门阀,就是指有权有势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就可以称之为门阀了。有权有势,那是指我们现在做了官,管理一方百姓,所以我们是很风光的。可是,官能够当一辈子吗,就算能当一辈子,子孙们怎么办?我们的余荫可以遮蔽他们多久?十年还是二十年?二十年以后呢?”
赵云、关兴若有所思。
关索不知这和土地兼并有何关系,不耐烦地说:“这我们都知道,不过我们问的是百姓有多少土地!”
董允无奈苦笑,正要回答,刘畅接口道:“三弟还不明白吗?休昭其实已经把其中的缘由说得很清楚了,官员们为了子孙后代有好的生活,为了家族的繁衍昌盛,就要想个一劳永逸的方法来解决……,三弟,你说这是什么方法?”
董允欣慰地微微点头,太子的脑筋转得很快,看来他果然是浪子回头了,也不枉我今日煞费苦心。
“什么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关索眨巴着眼睛,看看赵统、赵广,喜笑颜开,“我知道了,买田!”说完得意地看看赵统他们。
赵统、赵广家教甚严,还是不苟言笑的样子,让他很是泄气。
刘畅对言笑无忌的关索很喜欢,感觉就像是自己的亲弟弟,看他孩子气,笑着夸奖道:“三弟真聪明,这么快就想到了!”
董允噗嗤一声,忍不住笑出声来,沉闷的气氛
刘畅面色阴沉,盯着远处的庄园沉默不语。
大汉兼并之重,他还是知道一些的,黄巾之乱,便是因为土地兼并过于严重,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饥寒交迫,走投无路而发动的农民起义。
其实不要说黄巾之乱,就是历史上哪朝哪代,不是因为土地兼并而引发重大动乱呢。
人都是贪婪的,zhan有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醇酒、美人、金钱,只要是好的东西,人都希望zhan有。
农耕社会对土地的重视超过现代人的想象,土地对封建时代的人来说就意味着生存、美好的未来……
概括起来,土地就意味着一切!
于是,zhan有尽可能多的土地是家族繁衍壮大的根基,人们都不择手段地攫取。
帝王,占据着封建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是最大的地主,只是帝王是象征性的拥有,它需要有人来管理它的土地,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帝王从法理上对全国的土地拥有所有权,那是空的,是靠税收来体现的,真正拥有土地的是他的臣子。
作为帝王的各级管家,臣子们挖空心思兼并土地,成为他们私人的庄园,这些庄园向皇室进贡的税收微乎其微,绝大部分的税收都摊到普通百姓身上。
与各级官吏拥有良好关系的当地士族、土豪、地主,也转而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于是,实际肩负国家存亡重任的,都是无权无势的农户。
按照标准的封建社会基本单位——五口之家,应该拥有的土地是一百亩,虽然历代王朝都口口声声要减缓农民的负担,在初期也能够给与农民一定的优惠政策,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落实到底。
因为zhan有土地是帝王的各机管家和与之交好的士族、豪门、地主的基本渴求,那么兼并土地就无可避免的会随着王朝生命的增长而不断加剧。
农民一边要靠土地来挣得当天的口粮,一边要应付朝廷的征收,可自己所有的土地却越来越快的被豪强夺走,就算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豪强地主的佃客,沉重的税务负担仍然甩之不掉。
没有土地,还要面对凶神恶煞的税务官吏,失地农民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不得不逃走,成为流民。
而流民是没有生存手段的,盗贼、土匪甚至揭竿而起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造反,成了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出路!
造反之后又怎么样了呢?
不是被镇压,就是造反者成了新的大土地主,然后引起新的一轮兼并,在日积月累之后再一次爆发。
土地有尽而人无尽,人口土地之间的矛盾本来就是无可避免。
中国封建王朝轮回般乱后而治,治而复乱的根源便在于此!
但刘畅一直认为,造成一幕幕轮回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人口和土地不可调和的分配冲突,而在于历朝历代对农业的过度重视和对其他行业的过度压制。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土地是种植粮食的基本场所,说人口和土地不可调和的分配冲突不是主要原因似乎很矛盾,但刘畅从现代社会的经验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看法。
南宋王朝,百姓人口达到数千万,绝对不比除清朝后期以外的其他朝代人少,但拥有的土地却极少,而且年年面临异族入侵,该说早就该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了,可没有。
有宋一朝,农民起义也络绎不绝,梁山好汉的故事脍炙人口,方腊起义也轰轰烈烈,但这主要是花石纲等苛政引发的官逼民反,而非为了土地造反。
农民生活一直困苦,但还没到揭竿而起的地步,中国农民的忍耐力是惊人的,当然也是可悲的。
诚然,生产力和良种经济作物的培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刘畅认为关键不在这里。
刘畅认为,宋朝之所以运转正常,历三百一十九年,超过唐朝二百八十九年、明二百七十六年,甚至超过清朝的二百七十九年,其生命力如不是被异族入侵,还将更加漫长。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较好的解决了农商人口分流!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相对重商的封建王朝,士农工商各居其位,老百姓不必唯一靠土地吃饭,土地耕作不足,可以从交趾等粮食产区进口,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解决了大批人民的吃饭问题,最低限度的保证了老百姓活下去的最低要求。
刘畅不认为宋朝是一个完美社会,它的商业是初级化的,它的制度是僵化的,它的军队战斗力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但是同时,它的成就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辉煌的!
刘畅决心效法于宋朝制度,改进于它,适应较长历史时期的需要。
当然,他不会放弃皇家至高无上的地位!
人总是自私的,无私的奉献是美德,不过如果能够在社会义务与自身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刘畅不认为自己还需要将帝位拱手相让。
解决好帝王权利与百姓需要的矛盾,在制度上给予一定的制约,还是可以在保存皇统的基础上让国家发展壮大的。
至少,刘畅有信心在东西方文明开始交流的时候,由他创造的历史将远超他来那个时代的历史,取得辉煌的成就!
在管理的基础上开放一定的民主,可以在效率、创新和民主发展上起到良性的促进作用。
这是国家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之巅的保证。
刘畅的内心已经自动地将重新统一大汉的重任放在了一边,在他看来,这是不足一提的小问题,他任意拿出一项超时代的技术,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这个目标。
唯有建立一个可以长久运转良好、兼顾国家民族个人的政体,才是他需要殚精竭力的巨大任务。
这,或许会是一生的长久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