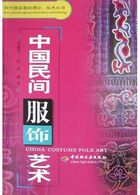载深如今是真的想搞死荣禄,此人后世他很是知道的,人很聪明,也有才能,有目光,认准了慈禧太后才是朝廷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况且,慈禧对他可是很不薄,作为旗人之中一个长的英俊潇洒,才敢非凡的年轻人,三十出头的荣禄,在辛酉政变之后,因为之前曾经一直被肃顺欺压的缘故,渐渐得到重用,他当然知道慈禧对自己好。
所以,虽然现在还没有后世那么多事,载深笃定的坚信,此人哪怕是才高八斗缺了他地球也玩不转,那也不是可以拉拢过来的人,一个亲王,一个太后,这之间的分量差的太多了。之前他得罪也算是个恩主的醇亲王奕譞,之后甘心在家“养病”。也充分说明了他不是个会屈服在亲王威仪之下的人。
既然不能拉拢,不能威服,又要在前头做绊脚石的话,那只好对不起了。载深动了杀心以后,反倒是卸下了一副重担。也许是一直以来养尊处优,身份矜贵的缘故,载深很少对人生出什么杀心来,今天下了这个决心之后,一扫之前的郁闷,吃的也欢畅起来。
“你二哥今儿这是怎么了?进了一趟宫,这就跟撞邪一样,沉了半天的脸,这会儿笑的跟个花痴一般,载濂,去去去,把人撵出去,把门关上,咱爷几个好好的聊聊。”奕誴一巴掌派在载濂脑袋上,摆出一副审问的架势。
载深哪有功夫应付他们爷几个?赶紧撒开腿开溜,这爷几个不是商量事情的人……载深想到这儿,忽然楞了一下,是啊,这事儿似乎满京城也找不着商量的人。
荣禄不是旁人,他的口碑极好,人缘也是极好,即便是跟醇亲王闹了点生分,但老七说起来总觉得有点对不住荣禄似的。平日里几乎就没听谁说过他的不是,呃,有,说他不是的人都死了,譬如肃顺。
如今满城满府的人,要找一个能共谋杀荣禄的人出来,却是千难万难。
只是想到肃顺,载深似有所悟。顿了一顿之后,朝奕誴几个笑道:“五叔,吃您的吧。这不是上头说要给指一房媳妇儿嘛,您想想您当年……咱五婶……”扯了个谎,夺路而逃。
真的是有正经事做,回了书房之后,亲笔写了一封信,想了想,觉得不妥,叫了一个平日里很信任的听差过来,也就是当年恭王府送过来的,打安德海事件过后就一直跟着载深的诚智,平日里都叫他诚四哥的,吩咐道:“诚四哥,明儿代我跑一趟盛京,路上二百两,够开销了吧?去奉天府叫他们派人,给我全城搜,找一个叫壁昌的红带子,容易的紧。找着了什么话也甭提,就说我说的,请他进京走一趟。五叔那边,你给我瞒着,自个儿找事由告假,这个事儿不能漏出去半点风声,可明白了?口要密,不止你,那个壁昌,也归你约束着。这人不是个好人,以前都兴阿在的时候,办过他好几趟抢占民女的案子,不过,他如今于我有用。你瞧着看,办完这趟差事,我叫六叔放你到外头驻防。那个壁昌,等我的口信——”载深做了个手刀的手势。
就这么的,这事总算堪堪的启了那么一个头。载深于两天之后,便见到了精神抖擞的荣禄,三十五六岁的年岁,能有什么病要养?递了牌子进府,立时召见,面上自然是一副很欣赏你的样子,寒暄着说了不少话,再切到旗务上的话题,说是此去盛京,还要王爷多多教诲云云。
载深自然是不信他的,敷衍着谈的很是尽兴,末了还留了一顿饭,席间不免的还要说起盛京上一次旗人闹事的消息,载深当然也要皱起眉头来说两句旗人真是没救了云云。谈话已毕,客人尽兴而归。
等死吧。载深看着他的背影登车,回身拱手道谢,脸上笑的很盛。
到底是满洲人之中提得上的能臣,荣禄在第二天就出京,几乎是跟诚四哥一块到的盛京,所以,在一个多月之后,载深见到壁昌的时候,很能听他说些荣禄刚上任,他还没赴京的几天里,新任盛京将军荣禄的作为。
荣禄告示的很明白,到任先办军务,整顿驻防左右翼,新军要给载深留面子,暂时不去动。壁昌惯了的察言观色,看得出来眼前这位年岁不大的恩主,对荣禄没什么好感,不然就不会巴巴的把自己从盛京拎到北京来了。
“姓荣的不是个东西,一来就说要左右翼学新军,起码的,出操要跟人家看齐,头一条,就是要精神。二爷爷您也知道的,咱们旗下大爷们能有什么精神?不止这条,到了盛京就说是王爷您的口谕,又他妈……又说要扣减咱们旗人的钱粮,还吹什么是王爷您的主意——”壁昌谑笑了一下,有些不屑的摇头道:“咱们盛京旗人最是知道王爷的了。咱们哪怕不相信朝廷,不相信官府,也得信王爷您,王爷是那样的人?先头就有人造过这谣,咱旗下爷们谁信了?他姓荣的又来这一套,扣了钱粮,还指望八旗兵丁好好给你出操?左右翼两总兵跟我都熟,来京之前请我酒说是送行,没少骂姓荣的那狗日的,早晚操不死丫的!”
“这就是你们的不是了,荣禄这也是实心任事嘛——”载深听说有人知道壁昌来京,不由得抬头看了诚四哥一眼,那边一脸委屈的样子。壁昌看出端倪,连忙解释道:“爷,可真不能怪诚四爷,是我,是我打小,一辈子没来过京城,新鲜的,乐呵的,两总兵跟我都铁,一块儿喝酒的时候,孙子我说漏了嘴了。不过爷您放心,孙子我也晓得里头轻重,再三跟他们说了的。”
载深哪里能信他这番话?呵呵笑着摆手道:“没事儿,来了就来了嘛,明儿你到宗人府去一趟,随便找个由头,做个进京办事的样儿。我骂你一顿完了。”
“哎,哎,我明白,明白。”壁昌人还是挺机灵的,低眉顺眼的压低了声音问道:“爷,可是有什么差事交给我办?”
“有——”载深知道这样的人最吃激将法,故意轻蔑的瞥了他一眼道:“就怕你没那个胆儿。”
“爷您这就是瞧不起人了——”壁昌擂着搓衣板一样的胸脯,涨红了脸道:“孙子我五岁那年就跟我阿妈上山猎过黑瞎子!长到如今二十三岁年,从来不知道个怕字儿怎么写!”
你丫当然不知道怕字怎么写……你倒是认字再这么吹啊!载深心中暗笑,嘴上却是赞许道:“那行!那这事儿就成了一半儿!还有一半,要看你口密不密。不过我信得过你!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只要你把这事儿给我办成了,少不了你一个外地驻防副都统!还是广州,杭州这样的好缺!今儿跟你说的话,你要是口不密出去乱说的话,有人问我我是绝不会承认的,攀诬亲王你大概是跑不了。”
激将在前,重赏在后,也由不得壁昌不砰然心动了。载深仍是要掉他的胃口,到得第二天在宗人府前斥骂了他一顿之后,才把要办的事情告诉了他。
当然,在宗人府斥骂他,是为了让里头知道,叫壁昌来京,是为了训斥他,叫他好生听朝廷的话,相信朝廷,相信官府,相信荣禄大人。回去之后,要好好的听话,不要再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唆,做出对不起朝廷的事情来。
这话当然是做戏用的,用于遮掩行踪暴露。正事,那是得他壁昌回到盛京才要办的。既然壁昌来京已经曝露,载深乐得再给他点甜头,叫诚四哥找不相干的人带他到京里各处消遣怡情的洗头房性质的场所逛了三天,打发了几百两银子下去,才把这么号人物送回了盛京。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等待了,载深接到谕旨,指婚纳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福晋,内务府老五也有旨意给他,那就是择最好的园子,尽速修葺,充作晟亲王府,以备成亲之用。当然,同治老哥这一会没被忘记,各地秀女也定下进京备挑的日子,兄弟两的大婚,也就在一两年之内了。
喜事盈门,当然有的忙活,加之正心庐舍的开学也到了紧锣密鼓的时候,载深忙活了好一阵子,这才等到了盛京传来的消息,血的消息。
荣禄定下的检阅盛京驻防左右翼军容出操的日子,比正心庐舍开幕的日子早了十天,比挑秀女的日子早了一个月,天津那边法国人打死一个县令,天津老百姓打死了不少洋人的日子里,京里忽然又接到了一桩听起来骇人听闻的事情——盛京将军荣禄,于检阅出操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兵丁出列跪在荣禄之前,口称有要事禀报,荣禄本身是个很会作秀的人,载深在京的时候常常背地里称呼他为大清梁朝伟,与后倾梁朝伟相映成趣的。遇上这种情形,大清梁朝伟当然不会放过显示自己不会摆架子的机会,躬身下来问他何事,并亲自接过那兵丁的条陈。
熟料那兵丁却是暗藏杀机,用的是图穷匕首见的老把式,在条陈之下暗藏的匕首,一下子扎进了就职盛京将军还未满一季的荣禄的心窝。
这是开国以来不曾有过的大事,军机处接到奏报以后,粗略一扫,不敢迟延,赶紧呈进御览。
封疆大吏出缺,比照城池失守,强敌入寇的火急军情,用的是六百里加急。而平常小事,是严禁用六百里加急的,所以,奕派人给载深传话也是语焉不详,只说封套上写的很明白:荣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