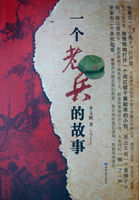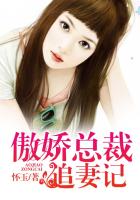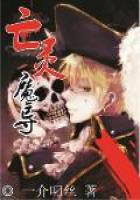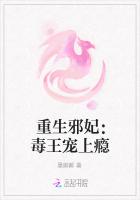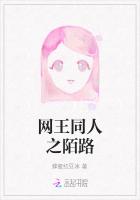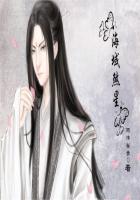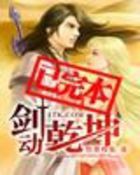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申出一个基本的观点:曾国藩文学理论及其创作上的成败得失都很明显地反映了时代环境和条件--中国近代固有的水土气候所造成的特点;曾国藩在文学方面尤其是在诗、古文方面的影响,不仅在咸同时期,而且在曾氏死后数十年的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影响是如何存在的呢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下面拟作概括性的分析考察。
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桐城派的再度振兴的确与曾国藩的极力倡导有关。
桐城派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至乾隆、嘉庆而大盛。它的宗旨是高举宋明程朱理学和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旗帜,阐发由此二者相结合而产生的“义法”。这样的宗旨正是符合了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因为继清初武力统一中国之后,到了康熙时期,清王朝统治者就想文武兼用,以承袭中国历代所传的道统和文统,使自己处于承接中国固有文化的正统地位,从而让民心归服。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刘大概、姚鼐等人都对这个宗旨谨守不移,从而就使得自己的文派在封建道义上占据着正统的地位,并在政治上得到了清王朝的支持,在理论上也得以自成一家。这样一来,在清王朝的兴盛时期,桐城派被视为中国文坛的正宗,其“义法”也就成了“钦定”
的学说。譬如,《古文约选》在乾隆时期就曾作为义法示范,“诏赐各学官”。可是,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桐城派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地位开始急转直下。
众所周知,文学为时代精神的最高体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离开它所处的时代,便失其生命,失其价值,而且,一代之文沿袭既久,诗文就不能发展,从而也就必然要发生变革。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敌入侵、内政腐败、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革的思想形成了一股社会新思潮,它在较大程度上冲击着封建守旧的文化根基。在文艺领域内,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文论家倡导变革,冲破束缚,他们提出文随时变、经世致用、自然为文、直抒胸臆的理论,逐渐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处于其对立面的桐城派首当其冲被加以否定和批判。桐城派文人在新的局势之下,提不出新的理论。虽然梅曾亮指出,“惟窃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也主张变革。但梅氏等人却主张仅变其文章所记的官职、时事和词句,不变其固有的“义法”和“神气”。这就使桐城派不得不在地主阶级改革派文论家们的批判冲击下败下阵来。再加上太平天国的革命扫荡,更使它元气大伤。然而,随着农民革命转入低潮,国内局势相对稳定,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和好”关系也逐渐建立,清政府为了重新加强它的统治力量,对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更为严格。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曾国藩接过桐城派的基本义理,高举“礼(理)学经世”的旗帜,与其师友、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刘蓉、郭嵩焘、方宗诚等人组成了“桐城一湘乡派”,提出更适应封建统治者需要的文艺主张,使得桐城派能够再度振兴起来。
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虽然接过了桐城派的旗帜,但他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在新的形势之下,对桐城派古文经过考察筛选,有区别、有选择、有目的地去接受,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创新。桐城派文论的实质是文道结合,因文见道,文以道约,但其文空洞,不切实际。曾国藩认为,如果继续全面继承这种文论体系,就不能使桐城派文论再度振兴。所以,他很明智地作出决定院“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既继承桐城派的基本宗旨,又“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使之“变化以臻于大”。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曾氏倡导“文章与世变相应”之说,来矫正桐城派文论的空疏之弊。为了使“文章与世变相应”,他特地在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这一纲领之中又加上“经济”这一内容,并且以“经济”为绳率。这里所说的“经济”二字,并非现代概念,而是明末清初由顾炎武等人提倡,在鸦片战争前后为魏源等人特别重视的经世致用之学。曾氏在这里加进“经济”一条,并以它为绳率,并不是要全面抛弃桐城派所谨守的“义理”,而是要弥补其“义理”中的空泛不实之处,通过具体实在的经世济民之学来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直接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以达到桐城派“义理”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正因为他重视“经济”--经世致用或经世济民的作用,并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他在把儒家的“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纳入“义理、考据、辞章”这一纲领时,就将“德行”、“政事”二科也都归入了“义理”的范畴之内。这样一来,桐城派所谨守的“义理”就有了具体、实际的内容,而不再是空华无实的了。从而,不管是从现实社会功效,还是从文学艺术观本身来看,曾氏对桐城派文论均有所创新。对此,胡适评论:“平心而论,古文学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韩愈至曾国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故桐城派的中兴,虽然没有什么大贡献,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他们有时自命为‘卫道,的圣贤,如方东树的攻击汉学,如林纾的攻击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以载道,的毒,未免不知分量。但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有人认为,桐城一湘乡派赖以维系的根本是曾国藩本人的政治势力,叶易在《论近代文坛的桐城派》一文中也认为它是由“政治权势组成”的。这个论断,我认为并不全面。诚然,桐城一湘乡派的崛起,与曾国藩本人的政治地位和整个曾氏集团的强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湘乡派毕竟是一个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学流派。这就是说,曾国藩首先是以“闳文系重望”而跻身上层,在爬上高位之前就颇负文名,特别是他以及他的师友、弟子乃至整个湘乡派的人物,在文学领域内如前所述,都提出了一套适合并反映时代环境和条件的新理论,并不是重复桐城派文论的空疏浅显之弊,而是在不少地方对桐城派作了改造。总之,曾国藩及其湘乡派,在中国近代文学体系方面,对总结、丰富和发展中国散文理论和创作方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是清咸同时期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固有特点的反映,同时也是这个特点所制约、促发的结果。
对于曾国藩在古文和诗歌理论与创作方面的成就,不管是他在世时还是在他死后一个多世纪里,人们都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评价。人们在肯定和赞扬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曾国藩的文学艺术观尤其是古文和诗歌创作理论对时人和后世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就时人而言,尤以曾门四大弟子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张裕钊受到的影响最为突出。
黎庶昌(1837-1897年),字莼斋,贵州遵义人。贡生出身。早年从着名学者郑珍和莫友芝治学,后有志于经世致用之学。1862年进京条陈时政见解,受左都御史李棠阶赏识,清廷亦嘉其言可用,赏其知县衔并发往曾国藩军营差委。1863年4月至安庆入曾幕,至1868年12月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前后跟随曾国藩达五年之久,受曾氏为人治事之学,特别是文学艺术观方面的影响相当深刻。黎自称未入曾幕前,读书识字,“虽欲抗志先哲而如幽乏烛”,入曾幕后学业日有长进,好“比回路之于仲尼”。他对于曾国藩在国势危难之际力挽桐城派古文之颓风的德行赞赏至极:“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途,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返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正是在曾国藩这种不因循、不守旧,对各家学说博采众长、兼蓄并用的思想影响之下,黎庶昌相应提出了“因时适变”的文学观点。这是因为,他与曾国藩一样,最初亦主守“文以载道”的观点,讲究“气味”、“格律”、“声色”,后来他在曾国藩学术观的影响下,对桐城派文体的弊端提出了批评,认识到文学与世道的密切关系,即作文与一个人的人生志趣以及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卫道”、“立言”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以曾国藩的文学理论和实践的社会功效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道光末年,风气尔然颓放极矣,湘乡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俊,朝夕论思,久之窥见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故其成就上者,经纶大业,翊赞中兴,次则谟谋帷幄。下亦不失为圭壁自饬、谨身寡过之士。”他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最终得出了“天地之运,积久必变”,“自古文章盛衰,与时高下”,文学应“因时适变”的结论。在曾国藩去世十七年后的1889年,他于出使日本期间编印了《续古文辞类纂曳一书。此书既是对姚鼐《古文辞类纂》的修订补充,又是对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中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在该书序言中他明确指出,之所以要将古文辞精华以新的面目展现出来,其目的主要是欲将桐城一湘乡派文论继续发扬光大,“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师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只格物,博辩训诂,一纳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车之饰。其道相资,无可偏废”。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人很重视学术上的师承关系。黎自成为曾的幕僚后,二人朝夕相处多年,建立了一种师生加父子般的深厚情意:“吾读书识字……无以辩于学之类歧,自遇公而始有师。……追随往复遂已十年及兹,分则僚属,而其饮食教诲不厌不倦,于我者视犹如子。”所以,黎庶昌在读书、治事、为人处世方面都谨“守曾国藩家法”,对曾氏文学观的继承自然无庸置疑。进而,因黎比曾晚死二十五年,其所处时代环境有了新变化,尤其是在出使西洋、日本诸国期间,他得以接触新知,这使得他对曾氏文学艺术观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发展。
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転,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副贡生出身。幼时苦读经书,后因时势刺激,决意弃八股试帖之学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1865年6月,曾国藩于北上“剿捻”途中张榜招贤,薛福成闻讯写下八大对策、洋洋万言之《上曾侯书》,往宝应附近曾氏座船献书。曾国藩读罢《上曾侯书》,击节称赞不已,遂延聘薛入幕。直至1871年,前后六年多时间里,薛一直跟随在曾国藩身边,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他在1885年所作《寄龛文存序》一文中,对曾国藩古文观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作了总体评价:
自淮以南,上溯长江,西至洞庭、沅、沣之交,东尽会稽,南逾服岭,言古文者,必宗桐城,号桐城派。其渊源所渐远矣。厥后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而所选《经史百这杂钞》,蒐罗极博;《文选》一书,甄录至百余首。故其为文,气清体闳,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蛲然者,几欲跨越前辈。
薛福成在这里,不仅指出曾国藩“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而且以《经史百家杂钞》和《文选》两书的特点来说明曾氏文学观的学术价值异常突出,既“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又几乎超过了他的前辈,体现出特有的学术地位和明显的社会功效。
吴汝纶(1840--1903年),字攀甫,安徽桐城人。进士出身。其父吴元甲,曾被曾国藩聘为家庭教师。吴汝纶自幼随父学经史诗文及科举之业,文名早显。1864年赴南京应江南乡试,中第九名举人;1865年入京会试,中第八名进士,以内阁中书用。曾国藩奇其文,延聘入幕。吴侍曾国藩前后达六年之久,因其坚实的文学功底,再加上曾国藩的亲切指点,吴氏对曾氏文学艺术观的理解较为全面且深刻。他的弟子贺涛等大多在古文方面有所建树,成为曾国藩的再传弟子。我们从《吴汝纶全集》收录的诗文、书信等第一手资料可见,吴汝纶对曾国藩的古文和诗词义法给予了全面肯定,并且在平常与张裕钊等人的切磋交流中加以阐扬和发展。对曾氏古文的地位,吴汝纶运用不同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他在给曾国藩的神道碑撰文时指出:“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又在《求阙斋读书记序》一文中说:“太傅曾文正公,学问奥博,贯穿今古,其于国朝顾氏、姚氏、尤所笃嗜者也。其读书必离析章句,条开理解,证据论议,墨注朱揩,自少至老,出入故者屡矣,而顾未始为书。”而且他认为《求阙斋读书记》,“其殆与顾姚二家着述相颉颃,何书不足数也。……盖公为学,不悦己而自足类如此。夫心之精微,不可以书见也。”对于曾国藩的古文和诗作观点及其学术地位,吴汝纶在《记古文四象后》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肯定:
往时汝纶从文正所,写藏其目次,公手定本有圈识,有评议,皆未及钞录。……谨依旧所藏目次,缮写成册。……自吾乡姚姬传氏以阴阳论文,至公而言益奇,剖析益精,于是有“四象”之说。又于四类中各析为二类,则由四而八焉。盖文之变,不可穷也如是。……文者,天地之精华,自孔氏以来,已预识天下之不丧斯文。后之世变,虽不可测知,天苟不丧中国之文,后君子读公此书,必有心知而笃好之者。是犹起姚氏、曾氏相诺唯于一堂也,岂不大幸矣哉!公又尝欲分古近体诗亦为四属,而别增“机神”一类,其后盖未成书。独于所钞十八家五言古诗,尝刻四类字朱印本。诗之下曰气、势、识、度,情韵皆与文同,曰工律则与文异,而无“机神”之说,盖仍用四类也。
由此可见,吴汝纶不仅是曾国藩文学艺术观的继承者,而且是桐城一湘乡派古文理论和诗歌创作基本精神的传播者。
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举人出身。其祖父辈均以文闻名于世。1850年,张氏以举人身份赴京,授内阁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