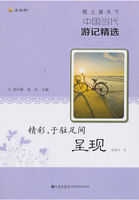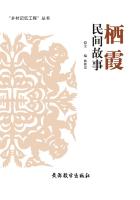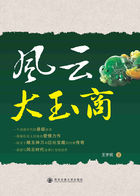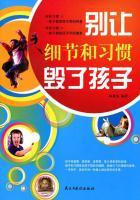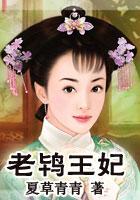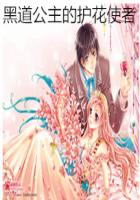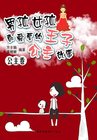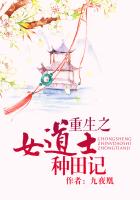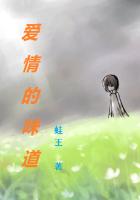对于张执浩来讲,生活的某些层面既不是高耸的铁塔,也不是突如其来的风暴,而更像一堆沙子:琐碎,庸常,以一种难以抗拒的平庸面貌腐蚀着诗人的梦想,对其心灵进行不动声色地谋杀。在《耸拉着》有这样表述的:“我们耸拉着/我们就这样饱食终日/孩子们在东扯西拉/他们挣扎着/长大成人/他们也要学习耸拉/学习如何在怀念中忍气吞声/”诗人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危机。但有时候,他只是表达了一种感伤和无法融入的思绪,而并不试图解决什么:“无论我经过哪儿/我都要承受/结石之痛……在这张生活的大豁嘴里/我数着被你们打落的牙齿/一天天/自学成人……他站在那双洗得灰白的解放鞋内/他站在自己的身体中/他的将来也在他的过去中/沉睡/多少前进的步伐也不能将他弄醒。”(《解放路》)这里面不仅有着心灵与现实的对立,还有着城乡间的文化对立,它们共同造成了生活之痛,使作者在这种感伤中陷得很深,以至于无法自拔。他的抒情大多带有感伤的色彩,虽然在后来由于与生活达成了和谐,也由于诗人采用了戏谑和戏剧化的艺术手法,使这种感伤色彩有所减轻,但他近来的诗作《这样写》和《给台风吹》表明,他在诗中仍未完全摆脱感伤的情绪。
在另外的某些情况下,诗人则在现实的淤泥中艰难地挪动双腿,期望在令人昏昏欲睡的生活咒语中,重新唤醒和确立自我:“我退出来/让时间喊疼/我/陷得太深/如同血液中的血液,也像是海洋里的水滴……如果今夜有月/我将把它端出大海/如果朝霞出来/我将从中取出/滚烫的髓岩/献给四周沉默的石雕”(《拔》)。从这首诗的前面来看,诗人希望改变生活的僵化秩序,把疼痛重新植入体内,“拔”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抽身离去,坚定果断的姿态,显示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来。但在诗的末尾部分,他却写道:“拔呀/我说/同时/我感到另一股力量正在拽我陷入绝境。”这个结尾是悲观和带有怀疑色彩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前面的英雄气概和决断的勇气,也使这两种对立的思想情绪扭结在一起,构成了诗歌的张力。这种矛盾的形成是源于诗人对于生活的反抗和绝望的双重体验。
第三种是与生活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和解,但并不是因为觉得生活的完美无缺形成的,而是意识到了生活的难度,从而将外在的挣扎和反抗转化为内在的理解和忍耐,诗人在诗中的语气变得平和起来,态度也显得豁达了许多,而将起先的那种悲剧性化解了。但由于这种和解不是在完全的洞悉和超越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就使得它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策略,是“化”中带“压”的,所以仍能从和解中发现裂缝,体味到一丝无奈的情绪来。
在《理想》一诗中,诗人表述的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情趣和责任,即儿子,丈夫和父亲三位一体的身份承袭和职责的履行,但张执浩在这里却用上了一个大词——理想。他淡化了“理想”这一词中的神圣和崇高色彩,而将它等同于一个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但这不意味着诗人的惰性或者责任的逃避,恰恰是能窥破生活的浮华,化绚烂为平凡,得其真味的生活智者所做出的自我承担和选择,也即诗人所说的:不高于生活,也不低于生活,而是与生活平行。这首诗中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和风格在张执浩诗歌中居于核心位置,可称之为他的核心诗之一。
3.怀旧与怀乡
张执浩是有一种怀旧情结的诗人,在诗歌中容易沉湎于过去,把最真切的情感通过忆旧的形式表现出来,唤起一丝温馨而带有感伤的思绪:“我就趋身前往/却不能抓住/河面上跳跃的水漂:/一连串的/与童年有关的下落……一双小手和一团绒毛相互抚摸着/‘天快要黑了!’/‘苹果一吃完/我们就回家。’”(《兔子》)他在这里潜回了童年,在村庄的小河边,找回了那只曾逃逸的兔子,使那种温暖和惺惺相惜的感觉再次降临。在另一首诗中,出现了稻草人的意象:“他是烈日之下的一截枯竹棍/是/仲夏夜的哨兵/他是张嘎/也是潘东子……无论我走到哪里/他总在那里/站着/张望着我内心的裂隙。”(《喂,稻草,人》)稻草人是乡村生活的一个典型事物,颜色金黄,形象蓬松,与广阔的田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安静而从容,闲适而温暖,所以作者才让他张望着自己“内心的裂隙”,这是一种对比,也是一种疗救。
可以看出,这些体验和回忆都是与乡村生活经验相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怀旧就相当于怀乡。故乡的人事、自我的成长道路和生活在其间的父亲母亲有如夕照下的影子,常以各种形式在诗中不经意地钻出来。对于张执浩而言,故乡意味着精神上难以割舍的联系,是灵魂的安息之所和诗意的重要源头。这种乡村生活经验是强大的,以至于作者的一些字根和意象都与其有关,比如:“米”和“白菜”这种特殊的意象。
他固执的将自己停留在时光的一隅,并非表明他不热爱当前的生活,只是可能在一方面,他试图拥抱生活;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所以他一方面在生长,一方面又在回望。怀乡既是一种情结,也是对于现实困境的一种解脱方式:“如今/我疼/我叫嚷着故乡的名字,也喊出了/一个浪子无名无姓的悲愤/我肯定是疼的/一如你无缘无故的/幸福/来得快了/也照样转瞬即逝。”(《大于一(组诗)》)生活之痛与怀乡纠缠在了一起。对于故乡的思念和回顾随着痛的深入而加深。张执浩倾向于把在都市中生活的自己称为“孤儿”,或者“农民的儿子”,这两个词显现了一种孤立和寻根的涵义,并且顽固地在生活中保持乡音,尽力地维持着自己与故乡或者说是“根”的联系。作为一个在都市中生活了多年的人,他的诗作却缺乏真正具有都市内涵的事物和生活场景。他保持着这样的姿态:“他站在那双洗得灰白的解放鞋内/他站在自己的身体中/他的将来也在他的过去中/沉睡/多少前进的步伐也不能将他弄醒。”(《解放路》)在一个喧嚣而繁华的都市背景下,他保持着一个乡村人的底色。这种对立是感伤而不和谐的,但也是作者所要坚持的。
另外,诗人虽然长时间地生活在都市,但他的诗歌对于真正带有都市气息和标志的场所几乎都没有涉及,不属于带有都市感的作品。对于都市,他涉及到的场所主要是家里的厨房,与厨房有关的菜场和个人的写作生活(实际上还是在家里),一旦涉及到其他的场所,就普遍带有一种调侃和讽刺的笔调。
4.爱与亲情
张执浩认为生活中不仅应该有真善美,更应该有爱,爱是构成生活的必要因素。爱对于张执浩显得尤为必要,这种爱在一方面会成为一种希望和拯救的力量,但在另一方面,却有可能使他更深切的发现生活的裂隙,与自身的气质相应和,而导致了更大程度上的感伤与悲观。
这其中既有可大而化之的,关于生活的爱。也有比较具体的:对于父母和妻儿的爱,对于朋友的爱,还包括一种对于下层人民的爱。但其中最为真挚的,是他对于母亲的爱,诗人的情感在他那些关于母亲的诗中得到了最深的沉淀。其实这也是他写的最好的诗作,他的抒情天赋因感情的深挚得到了尽情的展现,那种习惯提升和形而上修饰的倾向也得到了有效的节制。作者母亲的死,给了作者重重的一击,写下了许多思念母亲的诗作。他在《与父亲同眠》中写道:“夜晚如此漆黑/我们守在这口铁锅中/像还没有来得及被母亲洗干净的两双筷子/再也夹不起任何食物……我说父亲/让我再陪你一觉吧/话音刚落/就倒在母亲腾给我的/空白中。”他的生活从此被腾空,来盛下对于母亲的思念,这种思念必然是揪心而且缺憾的。故乡的炊烟不再升起,稻田里无人再次挥动镰刀,他和母亲只能在生死两界里独自徘徊,由爱与思念引起的,必然是至深的孤独绝望感。
而《全家福》这首诗的题目与他当时所面临的现实就形成了一个对比,揭示了现实永远的缺憾性。但他的思念之情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我们在时光深处放了一把躺椅/每当/耳畔响起吱呀声/我们就会跑步赶到/它的周围。”诗人仍然在内心深处不能面对这一现实,希望能改变生死的界限,让母亲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在诗的结尾,诗人念叨到:“早一天/他没出生/晚一天/您已过世。”在生与死之间仅有一天,在上一辈的母亲和下一辈的儿子的相处时光仅有一天。时光仿佛没有展开就已经结束了,在这些语句里潜伏了巨大的悲痛和没有终结的思念。
在《内心的工地》中,作者用高超的技法使得他与父母的联系达到了真正血脉相连的程度,他这么写道:“他必须洗净这从里到外的黑/才能看清/潜伏在他骨头里面的父亲/而母亲是看不见的。/母亲是空气/而母亲像工地上的灰尘/粘满了少年的肺叶。”父亲和母亲已经深入少年骨髓,他的存在就是他与父亲和母亲的同在。父母亲与作者的联系不仅是精神上的,更是血肉上的,是与生俱来和任何强力都不能改变的。
《青苗》是一首真挚的悼母诗,青苗不仅意味着故乡中的农作物,它在这里绝非意味着希望和安宁,而是蓬勃、杂乱,如火焰的灼烧与蔓延,用以表现作者的心绪,而青苗的这种一岁一枯荣的轮回秩序也反衬着死亡的永劫不复。
对于他的妻儿,诗人的笔触总是带有一种温情和呵护。其中《不真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首诗的词语轻盈,节奏顺畅柔曼。对男女关系的呈现摆脱了名的束缚和逻辑对立判断,回到了感觉的本初状态:“她说她愿意这样睡一辈子/抱着我/枕着我的右臂/和我毫无瓜葛/又千丝万缕……已经两夜了/我仍然什么也不是/既不虚伪/也不真实。”这两个男女在关系上既可毫无瓜葛,又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天两夜的温情在空气中挥散,但这里面的男女关系并不表现为一种胶合状态,而是无比自然和真实,他们之间既存在着温情和吸引,也保持了独立自在的状态。
诗人有一部分作品出现了下层民众的形象,最初他只是把下层民众作为审美对象或者纳入自己的生活场景范畴给予表现。比如《采石场》和《下午的菜市场》。最早表达出对于下层人民的人道关爱作品应该是《隆冬一瞥》,作者通过视觉印象对其做了速写似的刻画:“当他出来时/我们看见一块会走动的无烟煤,”作者在目睹这一情形后:“我感到头皮发紧/也感到烈火炽心/雪在下/但那人永远是黑的/我们看见了烧屋取暖的穷人/也看见了/从底下回来的幽灵/他磨磨蹭蹭/消失/在一只蚁穴里。”这种体会和关怀尽管还不够深入,但它表明了作者对于现实社会开始有了更多的关注。到了《少年与猴王》,他对下层民众的关怀不只是道义上的,也是对于人性层面上的:“他的工作是给猴群投掷苞谷/有过一次被母猴戏耍的经历/还有过许多次/被老板责骂的酸楚……江风吹送着三个美少女的圆臀/他说它们是氢气球/他又说:/猴王用阴茎杀人。”最后结尾处用了一句形式突兀,含义隐晦的话来表明少年的生理苦闷,这种生理上的压抑跟他的经济状况是相关的:“驻马店的童子到了湖北还是童子/十七岁/想女人/贫穷/无限期推迟了他的成人礼。”诗人的这种关怀是充分理解后的关怀,而非限于表层的同情,比以前的要深入得多。
5.隐喻的表达方式
张执浩经历了“写作的激情到生活的热情”,认识到写作就是在“内心的工地”不断地开掘勘探,而不是在高空架云梯,丰富的内心才可能成为写作的工地,诗歌就成了不断挖掘、开采情感的勘探者,诗人就像是一个在工地上忙碌的工作者。张执浩的诗歌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契合了当下凡世俗人的生存状态和审美取向,拉近了诗歌与读者的距离。他从生活中发现诗意,也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在生活中学会倾听,唱出了心中最真实的悸动和震颤,给人以温暖、信心。
张执浩善用隐喻,不是单纯地为语言增加所谓的文化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内涵。隐喻意在言词间造成一种“事物和意义相似性的辉煌映射。”张执浩诗歌中的隐喻是从事物本身出发的,缘自事物的本性,直接抵达人的内心。在张执浩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小美女”、“小女孩”、“蜻蜓”、“春天”等词,这些词语在诗歌中表达的是美丽、真诚、纯洁、甜蜜的象征,并不是被刻意标示出的一个与现实对峙的特例,它只是诗人对生活的一种抒情性的表达。在《高原上的野花》中诗人说:“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我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这里,在这里,我愿意/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我愿意终日涕泪横流,以此表达/我真的愿意/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这里的“小美女”与诗人一系列诗作中的“女孩”、“女婴”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都是指向一种纯洁、美好的事物,是与生活实在相连,和谐共处的。“祖国”意指诗人“内心的工地”,他要把内心投注在这里,建立精神的家园,实现心灵的栖居。“来历不明的小溪”和“涕泪横流”紧密呼应,是诗人缘自内心的“亲密的泪水”;“披头散发的老父亲”我们可以看成是诗人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之后,从一个将生活理想化的人成为一个与生活平行的人,不牵系于外物,不执着于妄念,通脱畅达。在《体力活》里,诗人这样写道:“我曾经拜访过牙医,让他/在我的龋齿里填充多余的疼”。“牙医”隐喻生活,而“多余的疼”则意指诗人不想也不愿意承担却不得不承担的琐碎,平庸和淡淡的悲凉、痛苦,是时间对诗人的击打和磨练。张执浩用这些平常的词语表达了生活的真实感受,既不刻意伪饰,也不故作姿态,顺手拈来,贴切自然,温暖贴心。张执浩对语言的把握,得力于他对生活的感受和触摸。他的每一个隐喻,看似平常,但都是一次对新的意义关系的发现和创造。它把词语从既定的语法修辞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