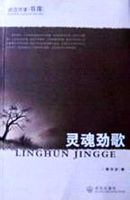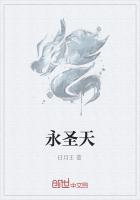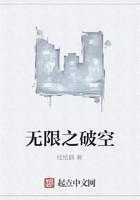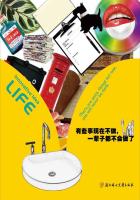白居易在诗歌方面的见解是:“文章合于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民情”。他主张诗歌应该反映现实,揭露和讽刺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反映广大民众的生活疾苦和愿望。这些主张,在这首词里无法见到。一方面,固然是短小的《一七令》无法包含更多的内容;又一方面,而且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首词已是白居易的晚年之作,这时候他已经失去早年的勃勃朝气了。他在这首词里只是表示出“能助欢笑,亦伤别离”。诗歌创作是应该反映现实、深入社会生活的,然而,生活在旧世界里的诗人,真正能始终坚持到底,似乎也并不是都很容易做到的。
柘枝词
白居易
柳暗长廊合,花深小院开。苍头铺锦褥,皓腕捧银杯。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将军拄球杖,看按柘枝来。
《柘枝词》的词调依柘枝舞而得名。一般认为,柘枝舞是由外族传人的一种舞曲,舞时让两位女童戴上系有金铃的舞帽,系上银带,绣罗宽袍,藏在莲花状的道具中,鼓声一响,莲花花瓣绽放,二女童轻盈地跃出而双双对舞,在翩翩起舞时,又有转动时所发出的美妙的声音。宋代的官乐有所谓由七十二小孩组成的柘枝队,穿上五颜六色的舞蹈服饰,逢上大宴,上场演出。《柘枝词》事实上是五言八句声诗体。
这是一首描写主人殷勤迎接客人来观看柘枝舞的词。而在东回的路上不断回头,朋友的踪迹是没有了,所看到的只是马蹄扬起的尘土。“去”“回”二字,既表现了送行人无可奈何的惆怅,又表现了他在行人去后孤寂与空虚的哀愁。而“一望尘”则把他恋恋不舍,一往情深描绘无遗。
词的最后二句“不觉别时红泪尽,归来无可更沾巾。”写的是送行人回来之后,悲痛欲绝的感受。分手之时,不知不觉中流尽了血泪,回来之后,还有什么东西能使手巾沾湿呢?写尽了别离的悲苦,真是“悲极噌干”。“红泪”,旧题晋王嘉《拾遗记》七《魏》说:“文帝(曹丕)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灵芸闻别父母,虚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后因称女子的眼泪为红泪,也泛指悲伤的眼泪或血泪。此处究指女子的泪,还是指悲伤的泪,难以确定,两种解释都说得通。
此词的情感抒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到分别后寂寞、惆怅,再到回家后内心极度的伤感,极富层次感,给人以很高的艺术享受。另外,此词用字朴实,不尚雕饰,也堪称一绝。
啰唝曲
刘采春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又
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
又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又
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
又
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
又
昨日北风寒,牵船浦里安。潮来打缆断,摇橹始知难。
刘采春是唐代著名歌妓,她与当时的一些文人、士大夫多有交往,尤其是元稹更为赏识她的才貌。在他见刘采春的《啰唝曲》后,大加赞赏。曾赠以诗云:“新妆巧样画双娥,漫裹常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纹波。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陆昶《历朝名嫒诗词》云:“浙人元微之(元稹)廉访浙东,见刘采春所作《啰唝曲》,赠诗叹赏。今玩其词,直是名家上等好笔,惜不知其人始末,如微之所赠诗庸甚,得毋为采春所笑。”这一评论颇为中肯。
《啰唝曲》又作《望夫歌》可见这几首词从头至尾是以描写闺妇盼望远行的丈夫归来为内容。啰唝也即来啰之意。
作者塑造了一个商人妻子的形象。唐代江南一带的商业很发达,商人为求利,长年累月在外经商不归,抛下家中年轻的妻子,忍受着痛苦的孤独生活。因此也引起了诗人们的注意,常以此作为诗词创作素材,李白《长干行》,白居易《琵琶行》即是此类作品的名篇。白居易则直言“商人重利轻别离”表现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为之发出沉痛的呼号。
刘采春身为一个女性,而且处于低层社会,她对世人的唯利是图,重利轻义的行为,更有深刻体会。所以她才能从不同角度细腻地描写出思妇的情怀。又由于作品使用了通俗民歌表现形式,所以更有大众性,故一时脍炙人口。
第一首是六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历来各种选本,常常单独成篇入选。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秦淮水即秦淮河,是长江下游的支流,在江苏省西南部。作者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地说出了心里话。她不喜欢秦淮水,最憎恨江上的行船。“不喜”与“生憎”在情绪上轻重变化不同。我们平常不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恨它,而恨这样东西,当然也就包含着不喜欢的因素,所以“生憎”比“不喜”更深重一层。为什么不喜欢江水,最恨江上船呢?这是因为水是间接的,而船是直接使她苦恼的原因。她的丈夫是走水路而去的,所以她“不喜秦淮水”,可只有水,他丈夫是去不成的,因为有了水上的船,才能“载儿夫婿,去”,故她最恨的还是“江上船”。
“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这后面两句就是这商人妇“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的原由。“载儿”的“儿”字是古时女子的自称,但刘采春在这种诗境中,巧妙地用了这一“儿”字,却给人一种伶仃、弱小、孤苦的感觉,细品其字别有滋味在心头。钟惺《名嫒诗归》浮其曰:“‘载儿夫婿去’句,‘儿’字口角可怜,‘载儿’字埋怨得妙。”看来钟惺对此字的理解是很深刻的。
“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与“不喜”“生憎”同样表现了不同深度的情绪。“经岁又经年”较之“载儿夫婿去”更为沉重。如果“载儿夫婿去”的船,能很快地将“夫婿”载回来,那么纵然离别也是暂时的,总有希望很快能团聚,也使人感到心安。可是“载儿夫婿”一去后,却过了一年又一年,长久不能相见,岂不更教人恼恨!这四句诗首联与尾联的前句与后句的层次是不同的,这也正是作者的用心之处。看似平铺直叙,实则深浅有度,轻重分明。她不直言恨夫,却言恨船,这种曲婉的用意表现了无可奈何的心态。恨人不知,惟将一腔愁恨发泄于眼前之物。
第二首“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东园是汉成帝时,邓成太后的陵园,位于汉宣帝陵之东,故称东园。后在诗词中,常以东园泛指一般园林。
作者眼前的柳树,可能真是一株枯柳,所以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她联想起自己枯燥、孤独、没有生机的生活处境,不恰如这枯柳一样吗?一株枯树有谁会去问津呢?只是使这女主人公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情怀。“枯来得几年”的“得”字很有一些深意。一是问这柳树枯了多少年了?二是问这枯柳,得多少年才能返青呢?这也正是隐藏在女主人公心底的一个问号,她的丈夫几时才能归来,以结束这寡居的生活呢?这就是女主人公见到枯柳,产生同病相怜的缘起。钟惺说:“‘得’字,问得宛曲”就是这个道理。
“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分”指缘分而言。说枯柳本来就没有生长枝叶的缘分,并非是太阳偏心,没有给它温暖的阳光,所以也就不必怨天尤人了。这显然是女主人公的自欺欺人之谈,就柳树本身而言,本来就能生长枝叶的,这是它的本能,怎谈没有缘分呢?之所以不长枝叶,当然是有许多客观因素造成的。夫妻常久别离,也并非无缘所致,乃是商人重利轻别离之故。这无非是她的自我解嘲,或说是自我安慰吧,总之,这是对于痛苦的现实,既无法回避,又无可奈何的表现。
第三首与第一首、二首在感情表现上有所不同。一首、二首均是借物泄怨,还有些委婉含蓄之处,对她丈夫“经岁又经年”不归,还在默默的忍耐,然而忍耐毕竟是有限的,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也终会爆发的。
第三首一开头就表现了怒不可遏的呼号:“莫作商人妇”,这当然不是大吵、大叫给别人听的,是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悲痛所激发出来的呼声,是内在的表现。过去有人评论此句说,这是作者劝导世上妇人千万莫作商人的妻子。可我们把上面的二首诗联系起来,从女主人公整个情绪的反映来看,此时的她,哪里还有劝导世人的心情?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可以理解,这正是她无法忍受孤寂生活,和盼夫失望后所进发出的沉痛哀号!那么,为什么会惹她竟如此恼恨呢?下面的几句就作了解答。
“金钗当卜钱。”金钱卜有的记载言汉代京房起就盛行了。一说:“古以钱记爻,至唐人始掷金钱问吉凶。”唐代于鹄诗:“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钗当卜钱。”(这首诗,又谓乃刘采春《啰唝曲》之七,下面将谈到。)清王士祯诗:“闺中若问金钱卜,秋风秋雨过灞桥。”在古典诗词中,金钱卜问吉凶的成分已淡薄,主要是用以卜远行人归期的。这里的女主人公没有用金钱,而是以金钗代替金钱作卜,金钗是女人信手拈来之物,使用方便,也暗示随时都可以问卜的,是常常要做的事。那么问卜的结果如何呢?她所日夜思念的丈夫归是不归?词中没有明显交待。但我们可以从词意中得到提示,问卜的结果告诉她,人会归来,她有了希望,所以“朝朝江口望”,可望的结果却是“错认几人船”,所谓“错认”是说本来不是她丈夫的归船,可她由于充满了希望,所以总是误以为她丈夫的归船。“朝朝”说明她不只是望过一次,而是天天去望,“几人船”也说明不是“错认”一次,而是无数次,希望越大,失望就越沉重,也就使她的痛苦与愤恨激增。所以说“莫作商人妇”,不能只看作是对世人的劝导,那只是表象,实际是在多次失望后的重大刺激下,所凝结起来的痛楚之言。
第三首已说明了她几次盼望,几次落空。那又为什么会落空呢?第四首给了正面回答,这是因为她丈夫来信了。
“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她回忆起当初离别时,二人讲的话。她丈夫对她说,他只到桐庐去(今属浙江省),“只道”二字,说明他当时并没有说还去别处。可结果怎样呢?“桐庐人不见”,说去“桐庐”可桐庐却没有这个人,这反衬出她丈夫的话并不可靠,或许没有讲真话。如果她丈夫根本就没去桐庐,那自然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了。如去了桐庐,然而又去了别处,那与“只道”二字也不相符合。不管如何,在女主人公眼里,丈夫是无信的。其实一个经商的人,对原计划突然有所改变,这是常事。但作为一个满腹怨气的思妇来说,却是不能容忍的,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她的钟情之深。
那么女主人公守在家里,并未外出,她如何知道“桐庐人不见”呢?这有两个理由。一则由于她久盼不归,也未见来信,必然要去信寻问,可却是杳无音信。如果他有了回信,她当然会知道他的归期的,也不至于“朝朝江口望”了。二则第四句里又有了交待。“今得广州书”,她终于得到来信了,可却不是从桐庐寄来的,而是从广州寄来的。即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女主人公得出了“桐庐人不见”的结论。
刘采春这首词,是在前人作品中演化出来的。《四溟诗话》载:“陆士衡(陆机)为周夫人《寄车骑》云:‘昔者得君书,闻君在高平,今者得君书,闻君在京城。’及观刘采春《啰唝曲》(从略)此二绝同意,作者粗直,述者深婉,然将种临敌不胜女兵,所谓小战则怯是也。”陆机的祖父作过丞相,陆机之父陆抗作过主管军事的大司马,他本人也曾在讨伐长沙王起兵时任后参军河北大都督,故称其为“将种”。所谓“将种临敌不胜女兵”正是在两首作品的比较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有“粗直”“深婉”之分。
刘采春所以敢用前人诗人词,正因为她有敢于“胜”前人的艺术魄力。我们把两首作品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其优劣。陆机的四句诗只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得到了对方的来信,知道了他的下落,其中并无感情色彩,和作者的主观情绪糅合在诗里,即所谓“粗直”。而刘采春的词,不仅交待清了对方的下落,同时揉进了感情成分。“只道在桐庐”“桐庐人不见”说明了对方的言而无信,从而揭示了女主人公盼夫归来的急切心理,和不归时的恼恨情绪。这就是此词的“深婉”之处。这也是刘采春胜人一筹的所在。
盼夫归已是失望,现在她所剩下的是什么呢?“顾影自怜”感叹人的老去,青春年华的虚度,正是她此时的心情。第五首就从这写起。“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这两句词看起来似乎词意相似,“今年老去年”只是“昨日胜今日”在范围上的扩大,但“昨日胜今日”却还有一层意思,是言人的变化是急剧的。只隔了一天,人就两样了,给人一种时间的急迫感。“今年老去年”正是“昨日胜今日”的积累,短时间看,感觉今日不如昨日;长时间看,却是今年比去年“老”多了。所以这两句虽然是互文,却有深浅程度的不同。
“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这两句说来使人伤心。人老,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只能老而愈老,却不能老而返童。作者说黄河也有变清的那一天,还是有希望的。可是白发(老年)是无论如何也再不能变黑(年轻)了,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那么,是不是说这位女主人公真就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呢?不能这样理解。这只是她失望的感叹,是对虚度青春年华的哀悼。作者以艺术夸张的手法,以示女主人公对寂寞生涯的深刻痛苦,和对年华流逝的沉重焦虑,而这痛苦与焦虑,时刻在困扰着她,使她心猿意马,终日不得安宁。这就使她不得不发出“奠作商人妇”的哀鸣!这种生动而沉痛的叙述,感人至深。黄周星《唐诗快》评其句云:“千古不刊之论,不意出自妇人口中。”称誉如此。
第六首“昨日北风寒,牵船浦里安。”女主人公虽然是痛苦的,且有牢骚,但她仍不失为一个善良女子的形象,她仍时刻关心着远离家乡的丈夫。“北风”象征着冬天的来临,所以着一“寒”字。冬天猛烈的北风,将会使江水卷起巨浪,这对船上的人是个严重威胁。于是她担心常在水路上来往的丈夫,要是遇见大风大浪可怎么办呢?她似乎在给丈夫出主意:“牵船浦里安”。浦是通往大河的水渠,如果在这狂风巨浪来到之时,把船牵引到水渠里停靠避风,那要比在大江大河里安全多了。因渠水流小,风浪自然会小。这只是女主人公的希望,她的话没法能让她丈夫听见。所以她仍然担心,要他真把船停在大江河里,很可能会造成“潮来打缆断”的危险。“缆”是系船的绳索,如断了,船就会失去控制而随波逐流,后果不堪设想,到那时才真是“摇橹始知难”了。靠着摇橹,拚命挣扎再靠上岸边,那时候才会知道是很困难的。作者为什么写作“始知难”呢?这个“始”字含义是深远的。表面上看,似乎是就事论事,好像说你没有按我的意思去做,把船牵到浦里停靠,将会造成危险后果,到那时你才知道困难呢。而更深一层的用意,还不止如此。通观六首,才能理解“始”字的作用,即仍是对商人重利轻别的幽怨,在词中委婉的表现。你(丈夫)长年在外不归,不管妻子的孤独与寂寞,不念家庭的温暖与妻子的情爱,到你遇见困难时,你才能真正的理解妻子的苦衷,你才会感到家庭生活的可贵,感受到家庭的幸福与安宁。这大约就是“始知难”的潜台词,也是整个六首的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