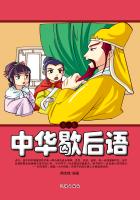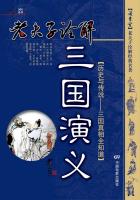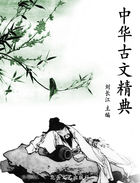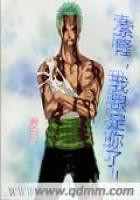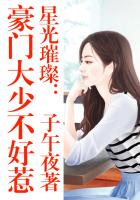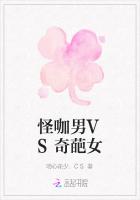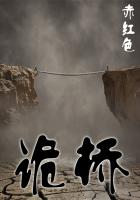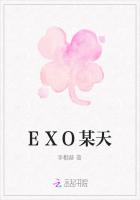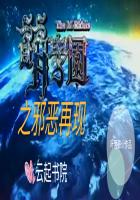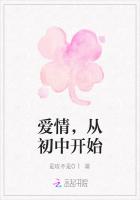古往今来,在这片苍茫的土地上发生过的那些金戈铁马,落日长河都已不见,留下的只有这片寂静。是非成败转头空,在自然面前,人总是微乎其微的。英雄迟暮,名将白头,天地万物的沧桑变幻真是无可奈何的悲哀。
兴亡谁人说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康熙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东巡之旅。
在中央集权的古代,帝王巡视地方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天子出巡在尧舜时期就已出现,殷商时期便有了用甲骨文记载的巡守之事。所谓守,是“诸侯为天子守土”,而“巡”通俗地说便是走出去看看。周朝后天子巡守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完善的制度,有着繁琐而复杂的礼仪。
康熙十年的第一次东巡祭祀了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和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告慰祖先“环宇一统”。如果说第一次东巡是为了完成顺治帝入关后祭祖的心愿,那么康熙第二次东巡则更有深意。
康熙二十一年,正是平三藩后的第二年,康熙一方面东巡“告祖”真正实现了全国统一,另一方面则着手解决了骚扰东北部已久的沙俄入侵。因此,这次东巡不仅祭祀了福、昭二陵,还远行至吉林祭祀埋葬了清朝远祖的永陵,借此视察了松花江水师和造船厂。纳兰作为康熙的近身侍卫,自然要扈从皇帝的出行。这次出行从北京出发,出山海关,渡松花江,历时八十天才返回了京城。
自古以来,山海关便被誉为天下第一关。南入渤海,北依燕山,不负山海之盛名。东巡时纳兰曾在这里停留,遍历山海关海天之色。山海关城东门“天下第一关”的匾额高1.5米,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萧显所书。
相传,萧显前后花了三个月时间酝酿,一挥而就完成了这幅千古巨制。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扁额上的“一”字不是题字时一起写上去的,而是用蘸满墨汁的笔抛向空中点上去的。
雄浑的山海关藏着别样的柔情。关内的孟姜女庙在这里演绎着家喻户晓的寻夫故事。纳兰在游历孟姜女庙时也不禁留下了感慨。
海色残阳影断霓,寒涛日夜女郎祠。翠钿尘网上蛛丝。
澄海楼高空极目,望夫石在且留题。六王如梦祖龙非。
——浣溪沙(姜女祠)
这词因景而起,落日残阳挂在薄薄的西天,余晖映在海面上,贴着涌动的浪涛,成一段虚渺的霓虹。冷冽的潮水不辞疲惫,姜女祠里日日夜夜听闻浪涛拍打礁石的动静。这祠又叫贞女祠,据说是为纪念那痴情哭动长城的孟姜女而建。
孟姜女寻夫的故事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孟姜女千里寻夫,化望夫石,看似柔弱的闺阁女子竟有着化石的执著与宁为玉碎的决绝。孟姜女的故事虽没有被正式记载于史书,只是以民间传说的形式在口头上传承,却流传了千年,越过了秦砖汉瓦,穿过了朝代的更迭。祠外滔滔江水,孤独的孟姜女在这里日日听潮声,看繁华过尽如云烟。正应了门前的那幅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姜女祠始建于宋代,纳兰看到的姜女祠是经过明朝修复后的。
姜女祠座落于凤凰山上,庙宇依山砌筑108磴行人石板梯道直通山门。108,在华夏文明的记录里,这个数字承载了太多的意义。《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封神榜》的108位诸神,北京大钟寺、苏州寒山寺每逢除夕等敲钟108下。这108级石梯,绝不是一个巧合。“扣一百八声者,一岁之意也,盖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正得此数”,明代学者朗瑛在《七修类稿》对108做了如此解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庙前的一百零八级台阶象征着孟姜女日日夜夜的守望,望而不见归人,到头来只得岁岁年年的失望。
希望,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它。希望,是珍宝,可讽刺的是与战争和疾病一起被装进潘多拉的盒子。那颗不会说话的蓝钻,被命名为“希望”,却在300多年间带给每一任持有人无一例外的厄运。如果说它是灾难,却每每在危急时焕发出神奇的魔力,上演一幕幕绝处逢生的戏剧。
纳兰在看到这姜女祠时不知是否参透了其中的真谛。海色残阳的光影里,辨不清是阳光给浮云涂了油彩,还是云彩给夕阳披了嫁衣,本就安宁的姜女祠因着隐约的涛声更加静谧。宁静的空间最易让人产生深沉的思想。
就像梭罗把自己流放到瓦尔登湖,远离喧闹的邻居和浓酽的咖啡,一个人践行着自然之子的生活。梭罗说:“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大约也同梭罗一样吧,纳兰需要面对人生,又或许面对的不只是自己的人生。什么是人生的本质?彪炳千古,称王称霸?纳兰有自己的答案,“六王如梦祖龙非”。
所谓六王,是战国时齐、楚、燕、韩、魏、赵六国,加上泰国主凑齐了战国七雄。当年魏国独霸终不敌齐秦两国后来居上,合纵连横的承诺终不敌一统中华的雄心。40万白骨深埋黄土,长平一战几乎预告了诸侯纷争的结束。如果假装听不到那些地下的哭声,后面的事看起来确是令人兴奋。从此,秦国的国王统一了货币,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南面称帝,以养四海。
再后来呢?所有的故事,浪漫的忧郁的激昂的落魄的,讲到后来都逃不过生老病死的大结局,“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吞八荒并六合盛极一时的始皇帝已安睡在当时还没挖掘出来的秦陵,彼时雄震天下的六王如今也不过是一个冷却的梦。我们意气风发地数风流人物,可背后等待的却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这词词题为“姜女庙”,写尽壮阔之景,博大之感,但事实并非单纯纪游之作,而是借游此庙发往古之幽思,抒今昔之感,欲抑先扬。纳兰饱读诗书,写词看似直白易懂,实际用典巧妙,句句锱铢,不论写景抒情,都是发自肺腑。忧郁沉敛的骨子里是对历史和现实更加敏感的认知和反思。单就这词,六王如梦祖龙非,思考就甚是凝重。
再细究:为何纳兰要用姜女祠来作为抒情的寄托和引子呢?
为修建长城,流的是百姓的血与泪,哭的百姓的累或亡。战争带来悲剧连连,人们却依旧为改朝换代互相争夺残杀。历史长卷不断翻看,怎目光所及,都是泊于苦痛之中的艰难百姓,叫人怎么忍心再读?
雨打风吹都似此,将军一去谁怜?画图曾见绿阴圆。旧时遗镞地,今日种瓜田。
系马南枝犹在否,萧萧欲下长川。九秋黄叶五更烟。止应摇落尽,不必问当年。
——临江仙(卢龙大树)
大树在此应指代将军树。《后汉书·冯异传》中记载东汉光武帝将领并坐在一起比拼军功,只有冯异独自在树下不与争功,得到了“大树将军”的美名。早些将军树便成了建立军功的象征。
这首临江仙中所提到的卢龙在现河北省东北部,地处山海关西南,自古便是连接山海关和京师的要塞。清朝时这里长期有重兵驻守,以拱卫京师和清东陵。飞将军李广曾经驻军卢龙地区。“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李将军箭穿石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提到李广,我们在感叹他青史英名的同时,也不由得想起那句“李广难封”吧。飞将军未去,卫青就不负众望地成为了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君君臣臣之间总是有太多的顾虑和猜忌。漠北一战中,李广任前将军迷失道路,便以一种武士的精神自决于疆场。
不得志的除了李广还有廉颇。
廉颇一直在等的老马嘶风的时代,以一句“尚能饭否”为结语,给他的英雄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过去征战的沙场,现在已成为百姓安居之所,这是普通人的幸事,却是一代英雄的悲哀。那曾经埋过白骨的大地此时更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怀抱着稻谷瓜果,怀抱着普通百姓的平凡的愿望。这一份变化,多少有些沧海桑田得令人措手不及。
当年的系马之处今日青藤蔓蔓,当年和着战马嘶鸣的北风经过了上千年的岁月也老成了一位老婆婆,轻柔地哼唱摇篮曲哄唱着小孩子们入梦。只是入夜时,老婆婆会不会想起年轻时候的往事?多少战功赫赫的将领,来不及转身便永远守走向了深沉的夜,留下一串不太稳当的脚印,和一个宽阔却有点真不起来的背影。老之将至,何必说当年?金戈铁马的硝烟散散尽,抬眼看,秦时明月依旧。
山重叠,悬崖一线天疑裂。天疑裂,断碑题字,古苔横啮。
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
——忆秦娥(龙潭口)
康熙二十一年的东巡远足至吉林。纳兰在这里所写的龙谭口是今吉林市东郊的龙潭山的一处古池,清代时在吉林府伊通州西南。
其实华夏大地上名为龙潭的地方很多,四川、重庆、河南和江西井冈山的龙潭,有的以山色秀美著称,有的以瀑布壮美闻名。由此也可以推断,能号称龙潭之处景观必然奇伟。据说吉林黑龙潭的石色青黑,泉眼深埋于潭底,从裂隙中的暗河涌出。传说东海龙王的第七子就在这里潜居,由此得名“龙潭”,清代还曾这里敕建黑龙王庙。
这首忆秦娥读起来不仅有豪气,还隐约藏着一股子冲冠怒气。山重叠,涧一线,天疑裂。当年岳飞以一曲满江红长叹,世人皆道岳飞所叹不过靖康耻未雪,功名前程尽废。而在纳兰胸中呢?或许还是那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纳兰及第近十年来常伴天子身边,后来更是擢升为康熙身边的侍卫。旁人眼里无上荣宠的生活,在他心里不过是蹉跎一场而已。那些记载着过去的碑文被人们用力地刻在石头上,却难以被人记在心里。人力的造作终不敌自然的造化。所谓功名,所谓权贵,转瞬间便湮灭于青苔之间。
古人常说,云从龙,风从虎。风起云动处,便是龙争虎斗之所。这里的龙潭人称水牢,仿佛水下便锁着蛟龙。蛟龙传说是有鳞的龙,得水便能兴云作雾,其声如牛鸣。忆秦娥上下两片均迭三字,仿佛是纳兰情不自禁叹两声,“蛟龙窟,蛟龙窟”,皇帝自命真龙化身,然而从古至今亡国的又哪个不是真龙天子呢?
千古兴亡,百年悲欢,于寻常人不过顷刻阅过的几页薄纸,有心人则借以追昔叹今。
独客单衾
纳兰随康熙的这次出巡经历了真正的北国之春。北国的春天,常常被戏称为春脖子短。寒冬刚过,却依旧有倒春寒来袭,难有江南早春鸟语花香的明媚。纳兰从什刹海的老家一路向北,虽不闻欸乃一声,却也见识到了山海相连的壮阔。然而这与他在京城的富贵乡太不同了。
车马劳顿之苦也让他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仿佛是亲人送别了一程又一程,山上水边都有亲人的身影,这漫漫长路终究有亲人一直不舍不弃的萦绕山光水色心间。
这里说的榆关依渝水得名,其实就是闻名天下的山海关。过去山海关一直被认为是长城的起点,与嘉峪关遥相呼应。康熙帝的这次东巡比十一年前的第一次东巡要盛大许多。
根据当在在清廷的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所记,东巡包括皇帝、后妃、皇子亲贵及随员侍从,一行总共约有七万人,在沿途行围还要抽调随围官兵。
一行人马由于使命在身皆是行色匆匆,只全身心的奔赴山海关。“夜深千帐灯”则是康熙帝率众人夜晚宿营,众多帐篷的灯光在漆黑夜幕的反衬下在所独有的壮观场景。
如此庞大的巡守队伍即使临时安营驻扎,“夜深千帐灯”是毫不夸张的。
在没有以假乱真的霓虹灯的年代,纯黑的夜,更像是一个舞台。风吹落,流星舞。地上千帐灯,天上流星落,与繁华对比的是灯火阑珊处的寂寞。
纳兰的寂寞需要留待一个无人的角落,需要自己去舔舐伤口,细细地品尝寂寞的滋味。此刻,帐外风雪大作,连一瞬间的失神也不肯留给他。人群中的热闹往往是孤独的,这一闹惊破了他思乡的情绪。
这个季节的会刹海冰雪已经消融了吧?湖边的虫唱鸟鸣,门外孩童的嬉戏声,夹杂着浅草的笑闹声。忽听“嘭”地一声,纳兰以为那是迎春花开的声音,其实不过是这寒风里的打更声。
用长相思的词牌谱思乡曲,更让这思念加重了几分。如果说思乡也是一种痛,那么入夜酣梦就是一支轻微的麻醉剂,可以暂时麻醉那根与心相连的思乡的神经。可生活总是残忍的,它偏要将人从梦境中清醒过来,生生地扯着这条敏感的神经,让这种不能说的痛钻进心底。
“故园无此声”,纳兰于这小令中题下了一份身在他乡的鉴定书,其实他心里又何尝没有一道逆否命题?此声非故园吧。
独客单衾谁念我,晓来凉雨飕飕。缄书欲寄又还休,个侬憔悴,禁得更添愁。
曾记年年三月病,而今病向深秋。卢龙风景白人头,药炉烟里,支枕听河流。
——临江仙(永平道中)
比之物理距离的疏远,精神世界的寂寥更令人难耐。
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沟通的意义,长期缺乏沟通的一对知己终会成为生命中的过客。古埃及的诗千里迢迢地来到中国,只讲了一句,“一个从来不变的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纳兰好似就是这样一个欲语还休的人。凉雨飕飕,引得纳兰的寒疾不请而来。被病痛折磨的纳兰是想寄封家书与最亲近的人一吐为快吧?
可是家书寄出去,不过平添家人的牵挂,于事无补,最后还是自己默默消化了这份思念。本是相互关心的人,以为少给对方增加烦恼便是对他好,殊不知这份假装的冷落要令人更痛上一千倍。
很多时候,人刻意忽略了自己的感受,以想当然的方式对待朋友和亲人,到头来却因多年的疏离与最亲近的人终成陌路。
纳兰说卢龙风景白人头,其实古今中外华发早生者常为多情恼,与帘外风何干?伍子胥一夜白头,心中所念不过一个愁字;东坡居士白日寄情沧海,夜阑风静时也长恨此生。景不为人所动,所以景得以长存,如秦时明月汉时关。而人因无情恼怒,因有情感伤,为踌躇于有情与无情的夹缝间而纠结,所以人最易老。纳兰在药炉前能做什么呢?看着袅袅升起的烟雾,听隐约的江水滔滔,眼前浮现的应是小桥流水的家园吧。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浣溪沙(小兀喇)
纳兰这里所写的小兀喇正是纳兰一姓祖先的居住地。纳兰一派,与佟佳氏、马佳氏、富察氏等并称为清初满族的八大姓。佟佳氏在康熙初年人称“佟半朝”,顺治帝的皇后、康熙帝的两任皇后都是佟佳氏。即使现代见到的佟姓人氏,大半也是满族人。与佟姓相似,现在的“那”姓,有很多都是“叶赫那拉”一家,也就是纳兰,蒙语中意为太阳。
纳兰的祖先为女真族的叶赫部,叶赫部首领金台石即纳兰的曾祖父,曾在努尔哈赤的战争中失败,自焚身亡。努尔哈赤为了平息部落间的敌对情绪,以联姻的方式成功地弥合了两大家族的仇恨。金台石的妹妹孟古嫁与努尔哈赤为皇后,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生母;雍正、乾隆两朝的皇后也都出自纳兰氏。这两个家族之间有着矛盾的联系:纳兰与爱新觉罗有着欺宗灭祖的仇恨,而爱新觉皇位的继承人身上都淌着纳兰氏的血。
饱读诗书的纳兰对先祖的故事自然很熟悉。在寒冷的小兀喇,在真正的冰封雪飘的国度,他看到的不是风一更雪一更的寂寞,而是那段被深深埋藏的历史。这是应是当年龙战地,蛟龙鳞动,血雨腥风。不过三四代之后,叶赫部的后人们集体健忘,绝口不提先祖金台石被逼身亡的过去,摇身一变成为了清廷的顺民甚至是炙手可热的权贵。
而康熙作为中原逐鹿的最大赢家自然是没有纳兰的这般思量,他以天下王土总占有者的姿态,在小兀喇也留下了感慨。
苍山岌嶪路绵延,野燎荒原起夕烟。
几点寒鸦宿枯树,半湾流水傍行旃。
——入乌拉境
康熙一挥笔,纵沾染着“枯藤老树昏鸦”的气息,可题下的仍是天子坐望苍山踏尽荒原的气魄。
从小便处于政治漩涡中的纳兰深知成王败寇的道理,如今的纳兰氏争做皇帝的忠臣干臣宠臣,当年战场上留下的壁垒就让它在斜阳乱草中荒芜吧。比之放弃权势,忘记是他们惟一而现实的选择。只是远处响起的名声,不知是为纪念那些远去的先人,还是为了提醒这位年轻有为的纳兰氏的后人,古今兴亡事,只待留给后人评说。
未得长无谓。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如斯者、古今能几?有限好春无限恨,没来由、短尽英雄气。暂觅个,柔乡避。
东君轻薄知何意。尽年年、愁红惨绿,添人憔悴。两鬓飘萧容易白,错把韶华虚费。便决计、疏狂休悔。但有玉人常照眼,向名花、美酒拼沉醉。天下事,公等在。
——金缕曲
塞外大漠孤烟
随王伴驾已经有些日子了,掐指算算,离回京的日子也不远了。又要结束一趟旅程,立于塞外的广袤天地之中,纳兰心生感慨。时日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指缝间溜走,可自己却还好像未曾活过一样。
想到自己苍白的人生,纳兰禁不住心生凄惶。心中所想所愿所盼之事,皆未能达成。每日所做的便是鞍前马后的侍奉帝王,仕途上的顺当,不能弥补纳兰心中的缺憾。
他所想要的不是什么荣华富贵。
可眼下,他除了荣华富贵,贫穷的一无所有。
在世人眼中,纳兰是含着金汤匙的贵公子。可是在他自己眼中,自己却是一个卑微无能的男人,他的一切都是父亲安排好的,他就像一个提线木偶,按照指令,步步照办,毫无生气可言。
在这静谧无声的夜晚,纳兰偷偷从帐中走出,除了巡逻的士兵的脚步声,四周一片沉寂。在这荒凉的大漠之上,能有什么声响呢?除了灌进耳朵里的风声,别无其他。
下雨了,雨声悉悉索索的声音,为这大漠增添了几份诡秘的色彩。睡意全无的纳兰就这样侧耳倾听着雨声。可是这萧萧的夜雨声,就如同愁苦之人拨弄琴瑟的弦声,凄凉震耳,声声敲痛着纳兰那颗充满愁思的心,也越发触动了他的情思,让他不自觉地回忆起了他曾经拥有的美好过去。
相思之情此时已如春日的野草一样,迅速的疯涨着,于是纳兰拿起笔,铺开纸笺,开始给所念之人写信,抒发自己的离愁别绪。
别绪如丝睡不成,哪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
书郑重,恨分明,天将愁味酿多情。起来呵手封题处,偏到鸳鸯两字冰。 ——鹧鸪天(别绪如丝睡不成)
这首词虽是塞上怀远之作,却仍然是相思的主题。首句“别绪如丝睡不成”,直抒胸臆,多情公子此时正在塞上,别后的相思之情让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而“那堪孤枕梦边城”则更进一步说明了纳兰的愁思之深。按照正常的理解,“梦边城”应该解释为“梦见边城”,但是联系上下文,我们就知道其应该解释为“梦于边城”。
紫塞,指的是北方边塞,鲍照在《芜城赋》中有“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的诗句。长城之下的泥土呈紫色,相传这是因为修筑长城的老百姓一批批全都死在城下,以至于“尸骨相支拄”,百姓的血肉之躯躯掺和了泥土,恰是紫色,所以边塞就被称紫塞。
在这样的场景中,纳兰却是一心想到了自己爱过的人。
“书郑重,恨分明”,容若在这里化用李商隐的“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李商隐的那首诗原是一首《无题》:
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裙钗芙蓉小,钗茸翡翠轻。
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
李商隐当时新婚不久,由于卷土了“牛李党争”,因此在仕途上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新妻子王氏并没有因李商隐在仕途上的不得志而放弃他,而是一直不离不弃,与其患难与共。于是李商隐写下了这首诗。
容若在此处截取“书郑重”和“恨分明”二语,可以看出,纳兰也想为自己的妻子写一封家书,报一下平安。可是卢氏已逝,留在家中的官氏并非自己如意中人,这封家书写了,又该寄往何处呢?
“起来呵手封题处,偏到鸳鸯两字冰。”纳兰写完了家书,想要合上信封,为信封签押,但签押到鸳鸯两字时,却发现笔尖被冻住了这是上天给的暗示吗?是不愿纳兰一生得以幸福美满吗?
塞外严寒,此时被冻住的,除了笔尖,还有纳兰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