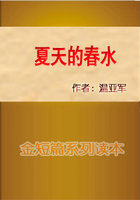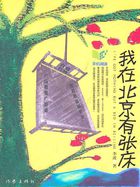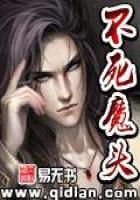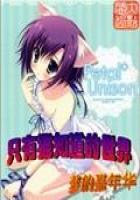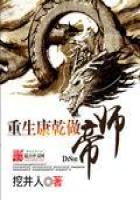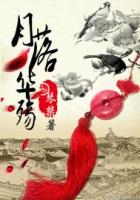正要进睡房,那王芳又一惊一乍地跑出来,手里拿了一袋凉拌鸡翅,热情得有些难以理解地说,来,谢姐,我们填一填肚子,正宗的“廖氏棒棒鸡”呢!这大一晚上了,是坨铁也软了!不由分说把谢芹拉到桌边。刚把那鸡翅铺开,手机却响了。王芳对着手机毫不遮掩地说,老娘回屋了,你他娘只出两百块,就想老娘陪你一个通宵,你把老娘当成大路货了呀!
谢芹听得心惊肉跳,趁她打电话,赶紧溜回自己房里。王芳打完电话,见谢芹已回到睡房里,把房门关得死死的,就哼了一声,轻声骂道,我以为你是个见得了祖宗、立得起牌坊的贞节烈妇呢,这半夜不归,会是啥好人?不晓得跟哪个野老公狂够了才回来!原来也是个偷鸡摸狗的货嘛,平素里装得像个脱了凡心的菩萨样,背地里不晓得有多淫荡,跟老娘也就是一路货色!
王芳一边大口吃那鸡翅,一边不停哼那首歌,像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一样兴奋。
谢芹躲在自己屋里,心里如一团乱麻。听得王芳在外面又接了一个电话,依旧是跟电话那头的男人讨价还价,最后讲定了,再加三百块。说完后,又出去了。
屋子里总算安静下来。她躺在床上,手里一直拿着手机,似乎那个李南无处不在,像到处乱走的夜风,像遍地流淌的月光。她忍不住拿出李南留下的那封信,却没有开灯,那信上的每一个字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就着窗外照进的一抹寒月,谢芹看着这封信,努力想象他写这些字的心情和形态,觉得那每一个字都是他月下的影子,乱纷纷一片,在自己心里一直不停地行走。她就在文字的尽头等他。
他却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冬天像一个老人,背着这个庞大而杂乱的城市,一步步往深里走。日夜里吹过不息的风,像老人的喘息,似乎能从这喘息中听到万物凋枯的声音。而那些大大小小的街巷,从早到晚却充满一种病态的温暖,到处弥漫着经日不散的热气,那热气里是稠密而醉人的烟火味。
这是苏明对这座都市的感觉,准确地说,是她对成都冬天的感觉。自从况二哥为了她,把那个李马华撵到渔塘淹死了,不得不从这座城里跑出去以来,苏明很少出去过,觉得像是得了一种再也好不了的病,对任何事渐渐没了兴趣,尤其厌恶做工程挣钱那号事。更是觉得,这些年,自己不过是给钱当了一个奴隶,整天在利益里耗,不仅耗掉了年华,还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尊严都搭上了,落下的就是那一堆放在银行的钱。到了今天,却反而觉得自己更穷,穷得似乎连这具身子都不是自己的。许久以来,她把这套布置精美的房子当成了最后的领地,觉得只要把自己关在这屋里,就能看到另一个确切的我,就觉得房外那一个我不过是一具影子。现在看来竟是如此可笑,可笑到连到底怎样才能骗过自己都不会。
就在这时,冬天却悄悄来了。冬天一来,许多东西将会被冻死,而另一些东西却又在暗自酝酿,要在冬天过去的时候生出新意来。那自己躲在这里是为了啥?是等着被冻死,还是等候一次新的花期?她不知道,只觉得,这注定是个充满了迷茫和挣扎的冬天。
此时,夜风在窗外不停地呜咽,像绵绵不绝的水,一浪一浪从窗口流过。她一任自己浸泡在这水一般的清寒里,觉得像是一块水里的石头,本想让那水把这身体洗濯干净,却偏偏长出了满身的青苔。仔细想来,这心里的挫败感,似乎全因了川北深山高木寺里那个枯木一般的老僧。老僧那几句偈语一直在心里回旋:
身在红尘里
万象皆为幻
苦海无尽头
何时能上岸
这字里字外的意思再明确不过,充其量是几句并不陌生的大白话,简单得如同一首童谣,毫无禅意;又像一碗清水,但喝下去时,却又觉得有许多滋味哽在心里,总是让人不安。更让她诧异的,还是与老僧的那次相遇,在那一片不可收拾的秋红里,在那座破败不堪的山寺中,她与那枯木似的老僧不期而遇,居然跟之前的一个梦完全吻合。到今天为止,她都不敢相信那是一次真实的经历,梦境与现实的完全重合,带给人的何只是震撼,那简直是一场承受不住的恐惧!这其中到底隐含着什么?是不是自己也遭遇了庄周梦蝶那样的经历?那么,又该怎样从中去领悟这一团迷雾似的混淆?她不知道,她只觉得是困在深林中的一只羔羊了,不知怎样才能获救。谁是我的上帝?上帝救得了我吗?
这个时候,她自然会想起宗教来,她找来一大堆各种各样有关宗教的书,逐字逐句充满虔信地咀嚼,期望能在某种顿悟之中,突然会有一只万能的手,为她启开洞悉一切本源的那道厚实的门,却反而在一种不可抗拒的疑惑中,觉得那根救命的稻草离自己越来越远。她获得的竟然是另一种失望。她极其悲哀地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进入不了宗教指向的那个世界。她觉得,骨子里总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在做着坚决的否定。那是世俗的力量吗?这力量到底缘自何处?
更让她可怕的是,她竟然在这段阅读和思考中,看到了宗教的虚弱和单薄。宗教已经越来越充分地融入到世俗生活中了,早已丧失了原本的纯净和圣洁。不仅如此,宗教在同世俗的不断妥协中,早已开始为人类在世俗生活中的种种行为提供规范与合理性。那么,生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诚然,宗教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人类自己创立了宗教,却又总是不断以非宗教的理性去考问、去衡量,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尴尬。那么,人类要拯救自己,是不是首先要拯救或还原宗教?或者,走到今天,宗教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需要另一种力量?需要寻求另一条路?
她不知道。
不知道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不知道才是围困自己最要命的力量。
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自己围困起来?
那么,放过自己吗?
此时,夜风似乎絮聒得有些累了,把有些寒冷的寂静还给了夜晚。一抹冷月从窗口泄进来,却无端让人生出一种陈旧感,使她不由得想起王右军的两句名言——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这分明是对生的无奈和死的恐惶,而这无奈和惶恐却穿过了几千年岁月,伴随人类生生不息的脚步,一直到了今天。到今天,却依旧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让人信服地消解这无奈和惶恐。唉,罢了,何苦让自己沉溺在这无奈和惶恐里不能自拔呢?还是逃避的好。逃避虽只是自我麻痹,是类似于手淫的自慰,历来被人诟病,但却是许多人离不了的鸦片。
她需要鸦片。
这时候,她似乎有些理解那些吸毒的人。
她在这清寒里轻轻长叹了一声。长叹之后,她决定放过自己。
这时,苏明决定上网。决定让自己再次逃往那个虚拟的世界。
那世界里有鸦片吗?
她要在网上去找那个“窗前明月”。已经许久没和他聊过了,自从知道,“窗前明月”就是在自己手下包工的那个委锁而庸俗的陈才以后,她有意无意地疏远了他。陈才与“窗前明月”在现实中的重合是残忍的。是对自己的惩戒吗?她不知道。但事后想来,自己的反应太强烈了些,陈才和“窗前明月”不过是被割裂了的两个人,一如被割裂了的自己。
这世上还有谁不曾被割裂?
她开始在好友群中寻找他,果然在线。许久不曾与他聊过了,却没给自己留下只言片语,这让她微微有些失望,有些伤感。他一定从自己的情绪里感到了什么。她有些犹豫地打下了两个字:
你好。
似乎略作迟疑,窗前明月回道:是你呀,流水天涯!你好吗?许久不见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流水天涯:近段时间很忙,没时间上来。
窗前明月:哦。身体好吗?
流水天涯:还好。只是冬天始来,有点不适应。你呢?
窗前明月:我很好,对冬天没啥特别反应。城里的冬天比乡下不一样,乡下的冬季,几乎每天早上都有厚厚一层霜。俗话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乡下的冬季是很漫长的。
流水天涯:我最爱听你讲乡下了,你讲的乡下就像是一首田园诗。你讲你的乡下时,你就是个诗人。
窗前明月:是吗?你真是说对了,我读中学时,特别喜欢写诗。老师说,我将来一定有大出息,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田园诗人。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却没钱去读,也就没有心思写诗了。
苏明不想听他说那些哀怨的往事,就打下了一行字:你就给我讲一讲乡下的冬天吧。
窗前明月:好的。我们那里的冬天一般从农历的九月底就开始了。冬天像是等在霜降前后的某个角落里,你在某一天早晨打开房门,看见地上有一层微白,以为是没有散去的残月呢。再看那衰草上,却似乎多了些重量,这就是初冬时节的霜,我们那里叫水霜。水霜一下,冬天就来了。你就见那些山,显得格外的瘦,树叶脱尽,那些平常间隐在林子里的岩沟壑,尽都显现出来。你一定会大吃一惊,原来这些山是这个样子呀!尽管这样的景象年年都会经历,但你还是会为之惊异。
流水天涯:你总是把你的家乡说得很美。
窗前明月:不是我说得很美,恰恰相反,我总是觉得我无论如何都说不出那种美来。它不像城市这么简单,我每次回到家乡,邻居们都要我给他们说城市,我就说那城里处处是高楼,街道很宽;人很多,车很多,很挤,人一走进去,立马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到处花花绿绿,到处是商店,什么东西都能买到。这就是城市的全部特点,很容易说清的。虽然我可能只是这城里的一个过客,但我却能很容易告诉别人一个完整的城市。当我来到城里,城里人要我描述乡村时,我却总是要遭遇一种尴尬,虽然我在乡村长大,熟悉乡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但我却总是不能准确地给别人讲述乡村,包括乡村的美丽和乡村生活的困苦。常常是刚给别人讲了,又觉得没有说对,或者没有说清。所以我觉得城市比乡村简单。
流水天涯:恰恰相反,正是你对城市生活缺少最本质的了解,所以你才觉得简单;因为你熟悉乡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你才有言之不尽的感觉。而真正的市井生活,并不像你看到的千篇一律的街道和楼房那样简单,只是你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过客,没有真正走进来罢了。你了解多少城市人的生活?你结识过多少城里人?
窗前明月:你以为我不了解你们城里人是吗?城里人只看重钱,没有钱就没有城里人的生活。你要是渴了,你能到城里人的家里讨一碗水喝?你要是身无分文,你能去城里人那里找一顿不要钱的饭吃?而在乡下,这一切都不是问题。这还不简单吗?城里人生活的全部就一个字——钱。
流水天涯:我不和你争论这些,我完全认同你讲给我的乡村的一切。我不打断你了,你说说你们乡下冬天的生活吧。
窗前明月:到了冬天,粮食早已收尽,有一句话说得好——春种夏锄,秋收冬藏。
流水天涯:你没说对吧,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是《千字文》里的两句。
窗前明月:我知道,但我们那里都这么说。一入冬,乡下人赢来一个最闲暇的季节。整整一个冬天,乡下人其实都在做着一种准备,就是准备过年。过年,在乡下人眼里是一件大事,乡下人对节日有一种朴素的虔诚。我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么一句话,说中国人对节气是非常看重的。这句话对又不对,其实只有乡下人才看重节气和时令,节气和时令与除乡下人之外的其他人没有关系。而春节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乡下人赋予春节的内涵格外丰富,所以得认真准备。到了冬月,关于过年的准备就开始了。只等第一场雪下来,几乎家家户户都先要熬糖,过去还要认真地煮一作酒。我没见过煮酒,但我知道私家煮酒的传统毁于后来的酒类专营。我曾无数次地听年老的人讲述家家煮酒的故事,让他们沉醉的不是那一作热腾腾的烧酒,而是煮酒的过程。我虽没有经历过那过程,但我却能从他们的热切里,听出那过程里的淳朴和痛快。我多次见过熬糖。兴茶办饭、煮酒熬糖是乡下女人的本份,我曾多次跟母亲一起熬糖。那多半是在一个雪夜,只有下雪天熬出的糖才够粘稠,才够纯甜。母亲一直守在灶前,糖水在锅里细细地沸腾,一蓬热气总在她周围缭绕,很温暖,也很细腻。我一直觉得母亲是把日子放进糖水里煮,那种感动是没有尽头的。
流水天涯:现在你们那里还熬糖呀?
窗前明月:不熬了,在乡下人的生活里,糖再也不是奢侈品。在那些简陋的商店里,随便可以买到各色各样的廉价糖。但我却觉得,只有母亲熬出的糖才是最地道、最醇厚的。
流水天涯:你把它诗意化了,但我喜欢被你诗化了的乡村。除了熬糖,还有什么?
窗前明月:也是到了冬月,挨家挨户开始杀年猪,其实,年已经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先杀哪家的猪,再杀哪家的猪,都是约定好了的。某家杀猪时,远远近近的乡亲都会聚到一起来,主人家会大办宴席,七大桌、八大碗,男男女女无一遗漏。所以,一般人家最少都要杀两口以上肥猪,一口全用来办了宴席。今天这家,明天那家,都会主动去凑那份热闹。平常间结下的梁子,尽都在这聚会中瓦解了。你会发现,这样的聚会是乡村不可缺少的,乡情就是在这样的交往中被一次次强化。其实,这种聚会在乡村是由来已久的,最初源于民间对神的祭祀。据说,早些年杀猪不是一件随便的事,要选好一个大吉的日子,更要举行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演变到后来,才成了全村老少的一次聚会。等到最后一家杀完了年猪,也是最后的一次聚会之后,年早已悄悄地来了,似乎有点唐突,有点猝不及防,但一切又都在流汤散水一般的既定日程里。
流水天涯:那你的乡村现在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