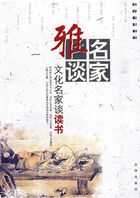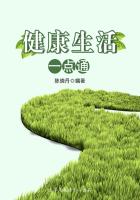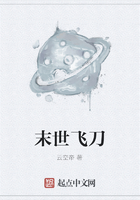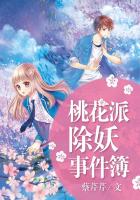重生命体验的诗歌创作存在着向形而上的精神气质靠拢的趋向,诗人们在不断拓展视野中提高自己的诗艺。90年代中期,鲁西西的诗不再局限于爱情题材,诗中的“我”逐渐被心灵的同道“我们”所置换,反映生活的面逐渐宽阔,诗作增加了对尘世生活的体察,显现出不同于一般女诗人的大气。鲁西西是运用其生命体验进行诗歌创作,其话语是剔除了女子气和女权主义话语的女性经验话语。《泛生活》中缠绕着醉语式的长句,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悲哀的女人自溺于寂寞的美酒中,“我经常是一个人——现在也是——握手、拥抱/一个人宵夜,一个人怀旧,一个人做爱/而且,我还以为,我或许并不存在”。长诗《在期待之中》与《明天见》在玩世不恭的语调下掩饰着生命的庄重静穆,语感流畅,语言机智俏皮,在断言碎语中闪烁着真理,带有一定的后现代倾向(《明天见》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期待之中》是诗人心路历程的展现,逐节展开追寻希望之光的过程,这是全诗的精神红线,它预示着诗人神性写作的开始。1999年,鲁西西皈依基督教,并于同年获得刘丽安诗歌奖。鲁西西的神性写作主要确立了尘世/天国的二元对立模式,表达了她对尘世的厌弃、怀疑和疏离以及对天国的向往、被拯救后的精神自足,主要体现在《诗篇》、《喜悦》、《死亡也是一件小事情》、《风的界面》、《我在这里》等诗篇中。宗教之于女诗人是一种逃避现实抵御尘世以获得精神自足的方式,也是维护个体精神尊严的方式。《我在这里》暗示着诗人从寂寞中自溺转为孤独中自救,“墙越来越厚,孤独越堆越高/我知道它们都是为了保护我/因为我不能胜任一个大环境/不能在四面季风的日子里静默,等候。”诗人对宗教所焕发的异样的热情和虔诚,实质上是她在尘世受压抑的激情之爱的转移,奔向一个理想的永恒的何西阿,她在诗中对神以亲切的“你”相称,源自她生命的根柢和呼吸的空气。浪迹云岭归来,韩少君的诗气象越来越宏大,《海中牧场》流淌着壮美的诗意,“大海正重复它的细节/水母白如花朵/盘旋着/和清晨一道,浮起/浓浓的清晨,像/原始公社的一碗血酒/正使一条鲸醒来/大海/你隆起,奔走/拖着满口袋水草、鲥鱼和白云”。柳宗宣的诗作自九十年代中期起,就开始“自觉地注重对个人诗歌中的当下性与现实性的关注,甚至私人感情的纳入”,《与诗人在小镇度的夜晚》、《当我们把电话放下》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那首《她穿过黑夜的楼顶回家》,失眠的男人敏锐地感觉深夜中的一切声响,对日常生活细节作慢镜头的处理,带有一定的实验性。
3.乡土与先锋
湖北是一个乡土诗大省,乡土诗作为湖北诗坛的传统,不可避免的对湖北先锋诗坛发生了影响,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先锋诗人,张执浩和余笑忠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写得异常出色的乡土题材作品。在张执浩的诗中,甚至出现了一种偏执,这种偏执导致了他对于城市调侃和讥讽,而对于乡村的追忆则是他感伤的缺口和焦虑的救赎。余笑忠则是借题发挥,将乡村的具体事物作为触发点,来抵达他那种具有沉思意味的诗情。此外,在韩少君、哨兵、柳宗宣、黑丰、刘洁岷、湖北青蛙等各时期的诗人诗作中,乡土题材也占到了一定比例。特别是诗人哨兵,自觉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洪湖的地域文化写作者,使他的绝大多数诗作都与洪湖有关。尽管这种对洪湖的抒写重点是其自在之态,但这种洪湖也是包含有乡土意味的洪湖,他对洪湖的抒写将不可避免的干涉到乡土因素。这种题材特色显现了这一时期湖北先锋诗坛的重要特色。
对先锋诗人来讲,题材不应该是写作的界限和问题,关键的是蕴于其中的艺术手法和生命意识。在张执浩看来,乡土是一个写作者的“来历”和“出处”,他之所以感怀,不是为了返回,而是为了出发。如果以题材而定的话,那么张执浩和余笑忠的很多诗歌都要归于乡土诗的行列,但如果从其中包含的生命意蕴来讲,他们的诗就跟传统的乡土诗有着很大区别。以往有相关学者对90年代兴起的“新乡土诗”的本质做过确切的描述:“新乡土诗的本质指向,是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是精神处于悬置状态的现代人类对劳动者与大自然的化合状态中呈现出的健康、朴素美德的追取,是以两栖人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社会在自己多重规范的生存空间无法忍受与兑付生命的情感时,对朴素、清贫、真诚、健康的美德的回溯”。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新乡土诗和先锋诗的一个差别:一个是乡土本位,另一个则是存在和体验本位。90年代的新乡土诗虽然摆脱了以往的那种对于乡村事物的表层抒写和留恋,从更深的程度上表达了个人的体验。但这种情感体验在最终指向的是“对朴素、清贫、真诚、健康的美德的回溯。”而对于先锋诗人而言,这种乡土的意象、题材和场景设置不在于单纯地表达他们对于乡村的热爱与情感,他们的精神指向在这里得到了替换和超越:一种精神指向是对于存在的叩问,而另一种则是借助这种乡村意象来表达对于个人生存的体验和感受。
这些先锋诗人在处理乡土题材时,突破了传统的抒情线路,将“乡土”这一词中所包含的家园意识和土地意识进一步提升,化为对于生命内蕴及存在的凝视和叩问。对他们而言,乡土一词所包含的地域性和文化内涵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乡土内容是如何与体验和存在交融,化为先锋诗人对自我和世界的感受和探求的。但这种先锋姿态与乡土在结合时,普遍带有浓厚的地方性的文化意味,体现出了探索和恒定的统一,精神内蕴和文化底蕴的统一。湖北的这批先锋诗人并没有走进语言的迷宫,尾随某些先锋诗人去玩弄语言,而是在这些乡土题材中反复的勾吊自己生命缝隙的沙砾,探寻自己的生存之境。
从这种先锋与乡土结合的成因来讲,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湖北的很多先锋诗人都是来自于农村,通过求学迁居城市,乡村是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地,最初的生命源泉和生命印记,这种经历会对他们一生的写作事业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入城后,他们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城市人,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乡下人。这种对于乡村和城市的双向疏离让他们在审视和体验记忆中的乡村经验时可能获得某种超越性的眼光,根据自己现有的经验不自觉的重组记忆,从而使乡村经验获得升腾的诗意。
当这些诗人在整合他们个人的经验时,我们能从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真正的乡土气息,诗中的经验表达和具体风物结合得比较紧,具有强烈的在场感,不仅能从中看到各种地域特色和风俗场景,而且能感受到他们对于乡土的天然亲近和内在体验。且这种体验不局限于此,有着进一步的超越。这种实在具体性和超越性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点跟其他省份的很多先锋诗人有所区别。比如小海也写村庄,但他笔下的村庄是一种神性的存在,不再是具体的,实在的村庄,看上去比较模糊而且抽象。他在诗中完全是用超越的眼光来感受存在的永恒,用个人的心灵对于存在独语。
而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乡土跟文学与人的灵魂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先锋文学中并不是摧毁人的以往认知和感受,而是一种超越性的姿态去深化和突破感受生存和进行审美更新,这种更新如果没有精神和灵魂探寻作为支撑,将变成破坏性的力量和单薄的形式主义。乡土题材看似保守,其实是无限接近灵魂的甬道之一。它应该也可以成为先锋文学中重要的精神和内容题材的来源。而湖北先锋诗人在调用这种乡土经验时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一切使先锋和乡土的结合成了湖北先锋诗坛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
(二)90年代湖北先锋诗坛的代表性诗人
1.此期湖北先锋诗坛的重要人物
在上世纪90年代,湖北先锋诗坛虽然在整体的作品质量上有所提高,但很多先锋诗人缺乏自己的清晰面目,于全国有影响的诗人并未增多,湖北先锋诗坛未能占领中国先锋诗坛的制高点,没有形成真正的繁荣局面。90年代属于湖北先锋诗坛的个体探索期或者诗坛发展期,作为80年代与新世纪连接的中介,为湖北先锋诗坛在下一阶段发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湖北先锋诗坛的很多诗人的写作跨度异常漫长,不仅跨年代,而且跨世纪。比如韩少君、柳宗宣、鲜例、阿毛、钱省、张作梗、黑丰、潘能军、鲁西西和刘洁岷等人从80年代就闯入了诗坛,很多人在2000年后还能在先锋诗坛保持活跃状态。他们经历了社会转型期的冷落和寂寞,依然执着于诗歌,在艺术修炼和精神探索上不断达到新的高度,这种群体的努力促成了湖北先锋诗坛的稳健发展,最终形成了新世纪以后的真正繁荣局面。
其中,最富代表性和面目清晰的先锋诗人是张执浩,及物写作的韩少君和女性诗人鲁西西(余笑忠其时已开始写作,有很多优秀的作品面世,但当时未引起诗坛的关注),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上一辈先锋诗人而言,他们的立场和情感显得更加温婉了,明显少了很多尖锐的东西,个人化的成分越来越重。这一方面是跟时代的转向、政治氛围的淡出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湖北省悠久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在先锋诗人们心灵中投射下的集体无意识。此期的湖北先锋诗坛的重要人物还包括:
韩少君,湖北荆门人,1964年出生,1983年开始诗歌创作,著有诗集《倾听》、《你喜欢的沙文主义》、《黄金日子》。他在转入先锋诗歌的创作后,善于运用口语和具体而冷静的意象呈现物和日常事态,来表达自身的那种精微而纤细的感受。当我们用理性和常识去审视和感受物时,往往意味着直觉和感性的死亡,而韩少君正是在这种对于物的呈现中,去重新感受物,甚至与物进行对话和神交,用句模糊而流行的术语说,就是“及物”。这种写作方式要求写作者对于诗歌表现力具有非常好的把控能力,是一种具有难度的写作。韩少君在完成很多出色作品的同时,也不免留下了一些遗憾。
李建春,1970年生,湖北大冶人。1993—1996年在广州工作,1997年回武汉。著有诗集《1991年自画像》(1992)、《个人的乐府》(1995—2006)。1997年获第三届刘丽安诗歌奖,2005年获《长江文艺》天问杯诗歌奖,2006年获首届宇龙诗歌奖。李建春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身份的诗人,诗歌关键词之一就是宗教,这一点跟鲁西西的后期写作颇为相像。在其诗中,“坚持于对生活的不屈服和称颂,显示出灵魂的韧性和深度来。其诗歌气质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严肃、执着和沉潜。语言忠厚睿智,内容凝重整洁,反讽但不失之于轻浮,执拗、直率而又保持着敏感和谦卑。这种风格可能不仅来源于其宗教体验,也来源于奥登、艾略特、叶芝等外国诗人的影响。此外,李建春的诗歌风格不只一种,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了多样的风格来。”
江雪,原名江山,湖北黄冈蕲春人,出生于1970年,著有诗集《汉族的果园》。1994年后因故停笔八年,2003年底复出。2005年5月创办解决先锋艺术网(一年后被封),10月创办先锋杂志《后天》至今。江雪的诗作雅致清新,同李建春一样,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较深,在诗中运用了较多的西方意象,且句法欧化,带有很浓重的翻译腔,是其诗歌的一大弊病。
剑南,原名卢雄飞,湖北省通城县人。其诗歌具有一种“唯美的古典主义风格,有着幽雅、忧郁而充满坚忍的力量”。同时,也带有一种“冥思的气质——神游、梦幻、空想、虚无,以及心如止水。那种无根的漂浮感和透明的易碎感带来了诗歌中无因的忧伤感”。剑男在诗中提到城市时,跟张执浩一样,总是充满了讥讽和批判的语调。
柳宗宣,湖北潜江人。出生于1960年,1987开始诗歌写作,出版有诗集《鹿脸》和《柳宗宣诗集》,1999年移居北京。柳宗宣的诗是一种温和而朴素的诗,充满了对于记忆和家园的回顾,给人一种静谧的忧伤感。在其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盛行的叙事性写法,据作者自陈,是受到了张曙光等人的影响”。此外,柳宗宣在诗中呈现出一种‘漫游者’的意识和姿态,”这种意识和姿态有时意味旁观和闲散,有时却意味着无根与生存的焦虑。
黑丰,原名丁世林,湖北公安县人,出生于1968年,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空孕》。黑丰的诗作在体现了九十年代诗歌的主要特征:“语言的口语化、叙事因素、个人化的经验和写作特征。黑丰的诗作具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表达着个人生活和历史的刺痛感,具有任性、幽独、纯粹、孤绝等特点。时代的风云变迁、个人的命途多舛在黑丰这里以更加细致的智性思索加以表现。”
2.90年代湖北的女性先锋诗人
湖北女性诗歌中的先锋诗人数量在80年代并不算少,其代表女诗人有华姿、雪村、胡鸿、乔迈等人。但进入90年代后,这些女诗人中,雪村离开了湖北诗坛,华姿和乔迈转行和改写其他文体,能保持诗歌创作中先锋姿态的已经很少。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女性先锋诗人是阿毛(这一时期出版诗集《为水所伤》1992、《至上的星星》1999)和鲁西西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后被集结为《再也不会消逝》),鲁西西和阿毛等人的女性身份不是作为宣言来表现的,而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诗歌气质。
阿毛在此阶段还未步入写作的黄金期,但此期的诗作已显露出一以贯之的纯美特性。鲁西西的写作时间则比较早,在80年代就步入写作生涯,并最终在90年代超越了华姿和雪村等人,进入了她生命中重要的写作阶段。她和阿毛两位女诗人恰恰代表了女诗人写作中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一个是柔软温暖,美好和思辨的,另一个是焦灼绝望,感性和情绪化的。